《马尔姆克罗格庄园》剧照
《马尔姆克罗格庄园》剧情介绍
马尔姆克罗格庄园电影免费高清在线观看全集。
羅馬尼亞新浪潮悍將培訏(《耐人尋味的追悼晚餐》,41屆)再向高難度挑戰。大地主的華麗莊園,請來客人留宿,屋外冰天雪地,室內討論熾熱。在飲飲食食之間,是連場對話,辯論宗教、戰爭、道德與死亡,觀點開始劇烈碰撞。仍是培訏的招牌長鏡頭,幾年前他取材俄國哲學家索洛維約夫的文本,以即興方式演繹成《三個道德練習》(38 屆),這次忠於原作,重構時代氛圍,考究人物談吐方式,鑽研服裝佈景細節,徹底回到文本的過去式時態。热播电视剧最新电影Fing头K王之王以吻之名小镇疑云第二季粉雄救兵:巴西篇机器人与弗兰克卢旺达饭店与艾琳的那个夏天我们都是动物美丽的精神新吊带袜天使毒花劫北京爱情故事最近的侦探真没用章鱼哥布袋人枪神传奇绝妙舞步仇念善良的男人美味情缘男人不醉时光巡逻队戴维斯夫人无处可逃无限商社2016:危机的公司职员少女与战车维京小海盗狗神杀出个黄昏恶魔之谜
羅馬尼亞新浪潮悍將培訏(《耐人尋味的追悼晚餐》,41屆)再向高難度挑戰。大地主的華麗莊園,請來客人留宿,屋外冰天雪地,室內討論熾熱。在飲飲食食之間,是連場對話,辯論宗教、戰爭、道德與死亡,觀點開始劇烈碰撞。仍是培訏的招牌長鏡頭,幾年前他取材俄國哲學家索洛維約夫的文本,以即興方式演繹成《三個道德練習》(38 屆),這次忠於原作,重構時代氛圍,考究人物談吐方式,鑽研服裝佈景細節,徹底回到文本的過去式時態。热播电视剧最新电影Fing头K王之王以吻之名小镇疑云第二季粉雄救兵:巴西篇机器人与弗兰克卢旺达饭店与艾琳的那个夏天我们都是动物美丽的精神新吊带袜天使毒花劫北京爱情故事最近的侦探真没用章鱼哥布袋人枪神传奇绝妙舞步仇念善良的男人美味情缘男人不醉时光巡逻队戴维斯夫人无处可逃无限商社2016:危机的公司职员少女与战车维京小海盗狗神杀出个黄昏恶魔之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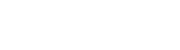
8.7/10. 两套不同空间的禁闭/纯粹的时间-影像,世纪交叠时刻的愁绪,死的迫在眉睫,民族认同的分崩离析,上帝在世的稀薄证据,不得不抓紧的复活信念……真正的幽灵时刻在于幕间的雪地穿行——那个不存在可能性的时间和不存在神义的空间,影像邀请鬼魂,隔离名唤为革命的静寂,在定时插入的仆人的圣洁白手间探讨这个即将到来的“敌基督的灰暗世纪”——同构于影像材质的劣化,这是所谓纯粹的柏格森影像的时刻。
当然可以这么拍。让角色一直对话没有任何问题,问题是我不想听这些陈词老调了,真的很无聊,给初中生上课去吧。
200分钟的对话意味着……眼中大部分的目光停留在读冗长不停的字幕,只有沉默或转场间隙才能瞥见精心设计的19世纪庄园;把话剧式情景搬到荧幕之上,对观众的挑战除了陷入模拟真实时间流逝的认知矛盾困境,还有对个人哲学宗教认知的考验:它无兴趣接近或与“yokel”们产生共鸣,分辨好战争和坏和平、真信仰和假信徒,地域观念和殖民倾向终归是信神者对异教徒的“圣战”
幽灵样的贵族统治者三小时喋喋不休,欧洲上世纪前半叶政治灾难(大概也指向眼下时代zz危机)之思想滥觞。某国可以翻拍个wb版。影片摄像构图美。
7.5分左右合适,片名不如叫"巴尔干最后的贵族们",主要是不同场景里的大段人物对话以及人物的凋零,如果有耐心听的话对话还是有趣的,甚至是能够引发观众辩论欲望的(我觉得有些回答没有抓住要点)
1900年的沙俄宗教哲学谈话录,移植到罗马尼亚的庄园,篡改了角色和结构,让法语演员照本宣科,再佐以精准的场景排设和镜头调度,把观者逼到看并思考着的抓狂边缘:Puiu已经走出新浪潮的现实很远了,不变的是对观影心智的高标准严要求。军国统治还是绝对非暴力,人性善恶和基督教义的关系,拥抱欧洲文明还是坚守民族根基?百年前的探讨有新格局的线索,法语的设定似乎透露了导演的态度。相比泯灭天使,它还是更与雷诺阿的游戏规则相映成趣:都是即将消逝的贵族群戏,后者的权力身份是平等而流动的,角色互动充满人性温度;这里关系是割裂而抽象的,角色困在形而上的语言游戏里,灾祸临头却丝毫改变不了谁的命运,从此变成孤魂野鬼,走入被遗忘的历史。秀才小兵各取所需没有压力,感觉导演这次表达的已经触及电影媒介的承载极限。
很独特震撼的一次观影,信仰哲学观念的碰撞,是对时代的反思,对自我的欺骗,对未来的指引,虽然未来充满弥漫,但我们依旧在一切险阻之中寻找善的踪迹。
很厉害。开场的几个深焦镜头就在封闭空间里“透视”出层次分明的“院落重重”;声音设计的混音层次也是被鲜明的区隔所拉开的,“words give the distance between them and the lack of a shared language”:第二章环境音的混响被明显拉大,主人们不自然的谈笑声和仆人们“moving gesture”,雄辩的和寡言的处于同一空间时故意弱化side-chain。只有镜头是最公平的:它的注视和运动均匀而神秘,Olga晕倒时的左右晃动,混乱发生时的“流连”。而它的沉默与窗外的钟声将之间的喧哗和高谈统统网罗于其中。
独特的语言类实时电影,导演通过漫无止尽的神学与哲学辩论和事无巨细的细节描写(侍者端茶递水,收拾餐桌,盖蜡烛等等),大量舍弃了电影的”省略“和”抽象“功能,使得我们在辩论中逐渐失去时间久暂的概念,只能通过侍者的上菜等行为来作为时间流动的作证,进而达到把观众困住——挑战观众作为信息收集和处理终端的极限的目的。影片中穿插的几处小插曲(Olga的晕倒,离奇的枪击,无法走动的老人),使庄园蒙上了一层神秘面纱的同时,映衬着影片中对于”死亡王国“的探讨;似乎一切都是虚妄,而只有死亡是注定的。
电影本身高密度且缺乏实际意义的文本似乎是造成疲劳的主谋,但相当优秀的场景和中前段镜头的优美移动极大程度上缓解了大脑的紧张。文本的内容在许多时刻令人皱眉,但翻来覆去的诡辩和逻辑置换至少能引起我大脑的活动,说一点都不爽也是骗人的。至于电影之外,关于其是否配得上被称为电影的讨论本身比电影中不同光谱贵族间的言语辩论更加令人摸不着头脑。这比去争吵何为神之国内的道德法则更加空洞。人家在讨论葡萄庄园比喻的出处,你们在讨论什么样的影像配称为电影,大家全都不如蘑菇。
俄国人后天习得的欧洲性抵抗血缘中的亚洲性,有时候端着的言行未能完全压制住本能,摄影机便从中失神,悄悄游移开。一年前在看这部,一年后还在看这部,究竟是谁困在庄园中了……
罗马尼亚导演普优的作品越来越长,也似乎越来越不考虑观众感受了。长达200分钟的新作的信息量超乎观众的接受能力,在五位角色滔滔不绝的对话里,讨论了战争与和平、善与恶、俄罗斯的东西方归属、欧洲文化、耶稣复活等等深奥的历史、哲学、宗教话题,没有一定的知识功底,很难坚持下来。其中不少观点独特,具有辩证的意味,引人深思,可惜高密度的展示令人难以消化。古装的服饰突出了舞台化的效果,非常像已故葡萄牙大师奥利维拉的仿古风格。中间一段突如其来的屠杀与最后讨论复活的一幕似乎在叙事文本上构成一种有趣的论证关系。
普优真的被电影耽误了,应该赶紧去剧场,没准还可以拿个罗马尼亚最高奖,拍成电影实在是没有必要,甚或说这不太是个电影。
6/10。开篇一个长镜头展现了苍茫雪地上的庄园外景,贵族们的狭隘与偏见都蕴含在这幅冷色调中,围绕饮食活动的人物聚散,军事、宗教、善恶各自主张的不断碰撞,旧世界的残党们远离了真实世界:将军夫人英格丽达大谈战争的崇高性,满脸不耐烦地说服其他人;爱德华鼓吹欧洲一体化和种族主义,认为俄国人应该界定为欧洲人;善良的奥尔加被反基督的几人大加挞伐。庄园内发生的谈话似乎是对旧世界格局崩溃的隐喻:大范围的对称构图,将人们围困在自己固化的阶层和思想中,卧病在床的老伯爵想参与讨论,只得到敷衍的作答,而仆人们永远是陪体,在画面中沉默穿行、收拾餐桌,一边是衣着富丽、强调和平与团结的名流,一边是因工作失误受罚的仆人,阶层差异的表现,以至于在餐厅遭枪击,贵族们慌忙逃窜、呼叫仆人时,仆人们都没有出现,看着贵族面对新时代的无措。
饶舌的俄罗斯文学,高谈阔论的旧俄上层阶级(法语),听不进去但赏心悦目的电影。那些考究的纵深走位,仆人像仪式般往复的动作和行动,无疑都是属于电影的美妙时刻
文本密度实在太强,只顾消化字幕而忽略运镜的取舍委实遗憾,开场就有大量视点的捕捉和游弋以形成某种进出画框的调度,人物站位的构图实在太奥利维拉了,尤其是餐桌戏的取景,门框是视线的中轴,有平面化的横移,也有来自景深处的信息涌动;那段神秘的枪战宛如漂浮在谈话中的幽灵显形,这是欧陆文明的回溯与展望,是新世界展开幕布之前几近沉暮的凝视,关于(绝对)善恶的鉴别,个体与群体暴/力形式的区分,宗教与人性本能的相符相悖,印象最深的仍是关于俄罗斯处于欧亚之间的站队——“欧洲人”已然成为一个精神概念。
室内剧,密度太大,扛不住了。别问我他讲了啥,因为我连电影名字都没记住
200分钟纯裸听生肉,五个人就这么在一间庄园里漫谈宗教、哲学、死亡,超长镜头超文学性对白,信息量超乎观众接受能力,普优已经完全不想照顾观众的感受去讲他的天生雄辩,这点快赶上锡兰的自我剖析能力了,化简为繁的旁征博引极易引起消化困难。唯一的优点是服化道相当考究,无差别还原20世纪初欧洲贵族的生活状态。
【X】对白电影被绕来绕去讲神态语调语音,不如大方承认从内容阅读上没有常人进入的空间。
正相反,我认为普优恰恰是在证明戏剧较之电影在某个层面上的不可为。观看体验仍是基于银幕长宽比的调度,且在漫长的段落中融化欣赏视角和雕琢有机时长,以摄影机运动来追踪舞台走位,剖解空间机理,进而无限逼近真实。阿尔伯特·塞拉的凝滞与繁衍并行的高维时空系统在普优作品里出现,似乎是冥冥之中,大概的区别在于后者暂时无法找到更好的动作来附身和消解台词的必要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