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想聊聊杜拉斯》剧情介绍
与玛格丽特·杜拉斯相伴两年后,扬·安德烈亚感到有必要和她倾诉:他与这位女作家之间的恋爱关系让他不再有任何自由,他需要用语言表达他的喜悦和痛苦。他请一位记者朋友对他进行采访,以便使她能更清楚地了解情况。他清晰而真诚地描述了他的故事的复杂性、他们的爱情以及他所受到的禁忌,那些千百年来女性所忍受的禁忌......热播电视剧最新电影百家拳之关门弟子达格纳姆制造涉过愤怒的海永远的托词柯明斯基理论第三季丑女也疯狂BeBeWinans的《我们三个国王》3年Z组银八老师千万别松手大烟山圣诞节南游记之闹三界计中计之密钥奇缘绝世千金第一季看不见听不见也爱你新街坊邻居走投无路的原偶像,选择与完全陌生的大叔一起生活翻译家~长崎翻译异闻~朋友也上床王朝第一季超市特工第二季夜校重返侏罗纪冒顿房间里的成年人海神密码银发的阿基多野牛花漾暖暖内含光名侦探柯南:独眼的残像
《我想聊聊杜拉斯》长篇影评
1 ) 《我想聊聊杜拉斯》:当谈论爱情时他们在谈论什么
1975年,扬·安德烈亚在影院看了杜拉斯导演的《印度之歌》,迷恋上了杜拉斯的电影和文学,从此一发不可收拾。
他们先是做了五年的笔友,终于在1980年见面,然后,27岁的扬·安德烈亚和66岁的杜拉斯同居了,直到1996年杜拉斯去世。
扬深度介入了杜拉斯此后的文学和影视创作,成为主人公,或共同创作。
扬因为杜拉斯,走进了文学史。
杜拉斯去世后,扬深居简出,生活和工作依然围绕着杜拉斯。
2014年,61岁的扬猝然离世,并与杜拉斯合葬。
两个人的爱情故事就是互相依赖互相折磨的故事,无数次争吵无数次祈求无数次和好,随意搜索关于杜拉斯和扬的文字,形容二人关系的关键词并不愉悦,“奴隶”“囚禁之恋”“扬是杜拉斯的情人、秘书、知己、演员、司机、护士和伴侣。
”读过杜拉斯小说或关于她的几部传记的人一定觉得所言不虚,但也确实困惑于这段煎熬又坚韧的感情何以至此。
文字有文字的解释,影像也有影像的理解。
《我想聊聊杜拉斯》(2021)根据1982年法国知名女记者米歇尔·芒索对杜扬·安德烈亚的真实采访录音改编而成。
当时扬与杜拉斯在一起刚两年。
芒索是杜拉斯的邻居和好友,这段采访也是杜拉斯同意的。
96分钟的电影几乎全是二人对话。
斯万·阿劳德和艾曼纽·德芙的表演细腻微妙,如临其境,如坐针毡。
一个人怎么会如此迷恋另一个人。
他原名叫扬·梅勒,杜拉斯“赐名”扬·安德烈亚。
“我与她文章的关系是统治与被统治的关系。
”“她变成一种毒品,我无法离开她。
”“我无法再看别的电影,无法与别人讨论她,会感到背叛,但我并不反感这种状态”“杜拉斯通过文字、影像创造了我”扬谈杜拉斯的文字,杜拉斯的电影,杜拉斯对他的掌控,杜拉斯的暴躁,杜拉斯对他的同性恋欲望的难以忍受,他与杜拉斯在一起时才能感到的欲望和迷恋。
“我是完整的存在着的人的对立面。
如果有谁以这样的方式存在,十倍于世上的其他人,那是玛格丽特。
十倍于世上的其他人!面对这样完整的存在,你荡然无存,全然虚无。
”他的爱情给他的语言加密,所有话语看得到,读不懂。
扬就这样喋喋不休、滔滔不绝地讲述着他和杜拉斯的关系,也许只有欧洲电影才喜欢拍90分钟哲思对话,也许只有法国人才会如此沉迷抽象思考情爱,也许只有文学家才会如此沉迷于用语言描述人与人,这是一场杜拉斯、扬和记者“共谋”的对话,当他们在谈论爱情时他们在谈论什么?
杜拉斯喜欢自己暴露自己,也享受别人解剖自己。
迷恋让爱情存在,痛苦让自我存在。
是文学家像文学一样活着,还是文学家活得像文学一样?
一部电影聊不完杜拉斯。
杜拉斯像一个过于早熟但又永远走不出青涩的女孩。
她也许最爱的就是自己。
扬爱的是疯狂爱杜拉斯的杜拉斯。
1984年出版的《情人》那段经典的开头,是在扬的注视下,杜拉斯写给自己的情书,是“爱”的某种极致。
我已经老了,有一天,在一处公共场所的大厅里,有一个男人向我走来。
他主动介绍自己,他对我说:“我认识你,我永远记得你。
那时候,你还很年轻,人人都说你美,现在我是特地来告诉你,对我来说,我觉得现在你比年轻的时候更美,那时你是年轻女人,与那时的面貌相比,我更爱你现在备受摧残的面容。
这个形象,我时常想到的,这个形象,只有我一个人能看到的,这个形象,我却永远不曾说起。
它就在那里,在无声无息之中,永远使人为之惊叹。
在所有的形象之中,只有它让我感到自悦自喜,只有它在那里,我才认识自己,感到心醉神迷。
2 ) 我们不能离开对方
此短文是基于背景知识的梳理文~不涉及电影术理论分析~全因Yann的文字。
我将离开这个没有你的世界。
什么时候?
你知道吗,我们知道我很快就会有一天死去吗?
是的,我们知道。
而且是在很长一段时间内。
然而,人们无法真正地去思考,好像只有生命是可以思考的。
死亡是一个陌生的东西。
好像它不存在一样。
然而。
(涉及剧透,建议看完片再看。
)--- 故事(Le Recit),Yann和Duras的相遇故事。
这个相遇故事里,Yann用了他的名,Duras用的是她的姓,因为Duras这么叫他,他从不称呼Duras,除了Vous(您)。
Duras更像是一个符号,一个全面的占有者,一个巨大的旗帜,一个永远无法刺透的光芒,具体的人叫不出口,Yann一次次诉说着,特别是Marguerite的真姓亦不是Duras。
他们的爱情故事的源起于杜拉斯的一本书Les Petits Chevaux de Tarquinia和一场电影India Song,看过书后的Yann沉迷于杜拉斯,越看越多越迷;在之后India song的见面会,yann拿Détruire, dit-elle找杜拉斯签名,请求通信,杜拉斯直接给出了巴黎的住址,这一通信就是5年(1975-1980),随后80年一日Yann用杜拉斯的真名找到她的电话,第一次通话良久,请求相见,被允许。
两人在 Trouville著名的hôtel des roches noires相见,这一见就再也没有真正分开(Yann去世之后骨灰葬于杜拉斯位于蒙帕纳斯的墓中)。
在一起之后的他们,杜拉斯让Yann做电影男主角(多部片),直接写书(L'Été 80)用他的名字写小说(Yann Andréa Steiner )给他。
全世界都知道他们相遇历程,杜拉斯去世之后,法国电视采访中,主持人都能详细叙述他们的相遇,以及Yann随后在这段感情里的“遭遇”。
---电影(Le Cinéma),难以自叙的事和完全投入的拍摄。
Yann的自我认同是男同,面对Duras,他的人生被颠覆,被击碎,被摧毁再被重塑,人生被重写。
电影旨在重现Michèle Manceaux于1983对Yann的录音采访,全部文字来自Je voudrais parler de Duras一书, 彼时Yann刚和杜拉斯在一起生活两年多,采访是杜拉斯许可的,甚至某个意义上是杜拉斯希望的。
Michèle Manceaux是法国很有名望的记者,也是杜拉斯在Neauphle的邻居、好友。
(此片能拍,也要感谢Yann已经去世的sister/soeur,是她从录音带一字一句做出了Je voudrais parler de Duras一书,导演表示拍摄之前和她见过,十分遗憾她没有能看到此片上映。
)Claire Simon的拍摄方式单纯、朴素且直接,有长达45分钟(片中有混剪进其他的内容)不间断的plan séquence(长镜头),而且与摄影师配合基本自己掌握景别(cadre)和部分剪辑,2周拍摄完毕,全片除了开头完全无音乐,收音和混音十分出色。。
巴黎首映之日,男主坦言若没有女主全力配合出演,自己是无法坚持那么久,哪怕有1-2分钟女主出戏,自己的表演就会完全垮掉。
一人一直说,一人基本听,看似简单,但随着时间的拉长,让人完全不出离其实颇难,Yann的话语,Swann的投入,Emmanuelle的专业加上技巧性调和,让一切变成可能。
这种本来不应该出现在电影上的历史时刻,活脱脱出现,以一种游离于背叛和遵循历史的艺术样貌重现。
好的电影人会给自己留有多种可能性,不会封闭艺术的想象空间,首映上,导演和男演员坦言拍摄之前都拒绝听原录音带,而只是从文字出发,用Yann的字为基造了这部片。
---爱(L‘amour),没有一种爱该被污名被诋毁?
杜拉斯写:在黑暗的房间里,我们彼此分开站立。
我们闭上眼睛。
我们看着他们,我们看到他们。
我们为他们的幸福而哭泣。
我们不能分享这种喜悦。
我们不想这样。
我们只能哭泣。
片中呈现的杜拉斯是极端的,自大的,嫉妒的,恐同的,暴君的,毁灭性的,完全掌控的,完全拥有的(posséder)。
(片中有直接的影像资料呈现她那令人厌恶的控制欲)。
但在这些之下,她对Yann的爱也是真实非幻的,是忠诚,扭曲的,无力的,无法挣脱的,她用她的无比强大留住了Yann(即使偶尔Yann会以暴力还之,片中用 Judith Fraggy的水彩画呈现)。
做为一个年迈的女人,她留住了她40岁之差的年轻同性爱人。
这种男权系统下的强大控制手法,极少出现在一个女人对一个男人身上,更少出现在书籍或大荧幕上。
且如首映导演所说,一个男人去谈自己的“爱”是不多见的事。
Yann大概真有特殊性格及作家心灵,自己逼出来这个采访,关于性、关于伤、关于抵抗和接受,关于他对杜拉斯的爱,一一呈现出来。
单纯想批判杜拉斯是gaslighting,会让一切单向化,扁平化,会像是质疑爱本身不存在一样的荒谬。
Yann去世前的影像资料里,谈起杜拉斯时的神采奕奕,开心愉悦,让我完全相信片中他的话,他就是那么无助又痛苦的“接受”(而不是忍受或被奴)了杜拉斯对他的一切,在爱里无法自拔,在爱里重新做人,他甚至觉得他的人生是从和杜拉斯在一起之后才开启的,面对杜拉斯说你不存在,他就欣然接受了,因为爱,因为那是她......Yann发新书的电视台的采访里,主持人冷酷无情的用杜拉斯对Yann所做的事情来刺激,明显侮辱Yann,Yann只是一直低头,不停重复说“不”....,“不是那样”,“不不”等等。
但说到杜拉斯对他的感情时,他抬头高声说très fidèle十分忠诚。
那一刻他的自豪掷地有声,放佛自己的爱被人一直污蔑,无法伸张,透过一句très fidèle,我意识到,他完成了对杜拉斯的拥有,那一刻全球皆爱的杜拉斯是仅仅属于他的,他有绝对的主权,原来完全占有竟在某个层面能达到变相性双向共通,大概爱真的有无数样貌和形式,不是只有平庸的对等和所谓正常的均衡,也许在一些人身上注定不与众同,只能但愿,那些不同不会被贴上标签,变成一场场风暴的祭祀品。
---尾。
很久没有用中文写长文了,竟然有一些些生疏感,不知道以后还会不会写。
这部电影给我带来很多想法和冲击,就想简短的记下一些首映所听和一些思绪,怕时间过去,溜走了,抓不回来。
仓促之余,若有错漏,烦请指出。
3 ) 听我倾诉爱情 一场纠结致死的独白
一旦那样爱过 之后的日子是被吞噬后的丧尸行走“She uncreated me to recreate me”她毁灭了我 为了让我重生现在我一人空居躯壳 如何重生她为我制作的电影里 我演着只有我能诠释的角色但镜头中 是死去的我一个我不认识的牵线皮囊但是她爱我她爱我有何错我爱至深爱到我的一切存在通过她的存在存在通过她活着而活着你们又有人真的在听吗性,情,支配,被支配,爱与被爱。
有人真的在听吗?
4 ) 电影表达形式很新颖,内容越听越不困
演技其实很好,能看出不是纪录片是演戏,但又不假,非常自然地还原一个敏感文艺的脆弱男人。
大段大段的表达,让我觉得真正的男主当年接受访问时就是这个状态,甚至说的就是一摸一样的话。
中间场景还原比较少,以谈话为主,夹杂少量真实的杜拉斯访谈录像。
一开始讲怎么相爱,他写了六年信后,杜拉斯提出见面,见面就接吻了。
那年他23岁,对杜拉斯从崇拜到欲望,过程好像是一周。
不对,好像是见面就有欲望。
讲同居生活时睡了一两分钟,醒来听到他说自己是同性恋,瞬间就不困了。
是第四爱呀?
后面两性关系越听越有趣,虽然他俩的恋爱设定比较戏剧,女方主导,还是虐恋。
男方是书粉,女方比男生大几十岁,社会地位也有差距。
能在一起就全部合理,因为爱情就是,出于本能、没有界限、爱恨交加;一方爱的多,一方就少;一方强势,一方就退让。
前面他控诉很多,抛弃家、工作来到她的城市她的住所,抛弃自我,从生活到思想上被控制。
没有自信,存在的意义是她,是服务于她。
但他说爱她。
他背叛,偶尔去公园见男人。
他逃跑,半夜去车站。
但他笑着说爱她。
电影结尾,高潮来了,他说,她纯真热烈,她才是爱里毫无保留的那方。
5 ) 我想聊聊我自己
近期摄入了太多关于“爱”的书、影、音,我想停下来反思一下自我。
年轻的杨的迷茫,绝望的爱。
对方又何尝不是?
你会爱上我跳跃的思维与破碎的文字。
我不认为同性恋是与生俱来的?
我爱我自己,爱同性的躯体,爱舒适区内的自洽;又或者无关性别。
我不知道是由于我天生便性向不同而爱上同性与异性,还是我个人的经历便可佐证现代社会爱对于性的依赖及两性的区分在被淡化。
真正内生的爱必然是双向的,我始终坚信不疑。
因为若我得知你无法爱上我由内而外的特点,也注定无法认同、进而爱上你。
我喜欢看你写字,将性格具象化为母语的横竖撇捺。
“停止无谓的复述,让阳光插进鼻息。
” 杜拉斯呢?
有远超对方的过往,生活经验与阅历。
我就是喜欢写字啊!
手而非脑的舞蹈。
我的老师,我爱你。
一切已然过去,外在的成功与改变也在重塑我的认知与生活。
是啊,你已成为我的一部分。
但我不认识你。
我爱你。
迷幻的魅力。
同性恋,自杀,死亡,蓬勃的朝气,离不开的爱,宿命的开始。
我时常想到你,我。
6 ) 迷恋
吸引我的不是电影本身,而是影片所呈现的一种奇异存在——被绝对的激情所占据的灵魂。
柏拉图讲述诗人的迷狂,基督教语境下圣特雷莎的迷狂,巫文化中萨满的迷狂,都是与超验世界的通灵,人作为有限的造物与无限相连的非理性的窄门;人的身体成为神灵降生的寓所。
伯格曼《处女泉》的结尾,死去的少女就成为了这样一座神迹涌现的圣殿。
超验的激情在世俗化进程中被心理学及生物神经学术语解释为一种谵妄,现代世界所遗落的唯一神迹似乎只剩浪漫爱的神话:激情的对象不再是超验存在,而成了世俗之人。
尽管在有关命运的暗示中,还能依稀辨别出信仰的遗迹。
《我想聊聊杜拉斯》呈现的就是这种世俗化的激情:一个人对另一个人所能产生的最极致的迷恋。
影片再现了一次真实的访谈,被访者是扬·莱梅,他更多地被称作扬·安德烈——这是杜拉斯为他创造的名字。
他是同性恋者,哲学系学生,写过一些口碑不佳的小说,然而这些轶闻只因他与杜拉斯的关系才获得了被谈论的价值;他只能透过杜拉斯而存在。
扬是杜拉斯晚年的情人、杜拉斯电影中的模特、杜拉斯某部小说的人物原型;访谈围绕杜拉斯展开,访谈场所在杜拉斯的公寓,而扬在访谈中说出的第一句话是:我想聊聊杜拉斯。
有时,他甚至都不能被视为一个完整的情人,而更像杜拉斯唇边的一个音节,杜拉斯情欲的一次折射,杜拉斯暮年的一句梦呓,是杜拉斯在小说家,电影导演、社会活动家之外的又一重生命变奏;扬·安德烈,只是杜拉斯的一个别名。
他们的关系中自然包含着支配、控制与暴力,只是这暴力的核心是激情,这种激情甚至在两人相遇前就已然将扬摧毁、重塑。
他用“被击中”“被捕获”形容初次遭逢杜拉斯小说的战栗。
许多人为杜拉斯着迷,但极少有人会将一种阅读体验下沉为存在经验,将文学介质体会为一个独特灵魂的亲临。
享乐的美学之旅被转变为暴烈、可怖的伦理学事件——这是扬受难的开始。
某种意义上,扬是天生的信徒:他拥有弃绝自我、献出自我、令自我被他者全然占据的神圣天性。
生命化作朝向外部的激情本身,这一激情的强度、密度、力度令此前所有的生命经历都变得虚假不实、恍若隔世的幻影。
德勒兹认为人的特异性在于存在的强度。
扬被杜拉斯吸引,就像微小的铁片不受控制地吸附住巨大的磁石。
“我是完整存在的对立面……如果世界上有任何人能够以完整的方式存在,那就是玛格丽特……面对这样完整的存在,你只能作为非存在与虚无。
”杜拉斯谈论事物的语言,看待世界的方式,她的写作、激情、甚至料理,都拥有扬无从企及的真实。
扬对世界的体察永远无法像她那样精准、深入,他所使用的语言永远无法那样恰切、生动,他的人生领会永远不能到达直见性命的程度;在杜拉斯强烈、完整、近乎暴力的存在面前,扬就像残缺、虚弱、愚钝的影子,只能在身后捡拾巨人遗落的只言片语,等候贫瘠身体中抽长的残芽。
生命是不公的,有时天才的几笔涂鸦、几句戏语,就已然包含着常人一生无法抵达的强度。
《莫扎特传》正是对这一残酷差异的深刻揭示。
萨列里是与莫扎特同时代的作曲家,也曾显赫一时、受皇室重用、被妇孺传唱,然而正因站在匠人与天才的边界线上,他比任何人都更清楚自己与莫扎特之间痛苦的、无法跨越的距离:上帝在其心中种下歌咏的欲望,却拒绝给予其天资。
暮年的萨列里在疯人院中弹奏旧日的作品,而年轻的神父只能轻声哼唱出莫扎特的小夜曲,萨列里写下的旋律早已在时间的风暴中沉落为一捧灰烬。
《情迷六月花》中,乌玛·瑟曼所饰演的亨利·米勒之妻愿意跟随米勒,正是希望借由他的才华获得在文学中不朽的存在——这是缪斯的野心。
扬并不嫉妒杜拉斯,也不渴盼被塑造为不朽的艺术形象;他的激情带来的是完全的献身与极致的迷恋。
尽管在民主时代的理性话语和身份政治的主体崇拜之下,这种激情往往被指认为愚昧和疯狂。
按今天的流行语,扬是无可救药的恋爱脑、被精神控制的受害者,杜拉斯则是Art Monster,是典型的NPD、是PUA大师。
这种关系并非一种情爱关系,而是彻底的权力关系与利益关系,充满剥削、控制与伤害。
当代情感话语的圭臬是情绪价值、及时止损、爱自己、主体性,是避免疼痛、追求舒适的消费主义延伸,是将“情欲”二字解析为激素和荷尔蒙的生物还原论;扬的迷狂早已被扫落进一个灰暗、矇昧、不可理喻的旧日世界了。
杜拉斯从不使用浪漫爱的话语,她所拥有的是激情、欲望与毁灭的语言:我会摧毁你,然后创造你。
我要享乐,要同你做爱。
这并非爱的表达,而是面对一种纯粹、致命的激情时所能作出的最为恰切的回应。
入迷者、深陷情欲者、被他者全然贯穿的“非存在”与“虚无”的游魂,所能聆听的也唯有塞壬的歌声。
我并不否认激情所必然携带的暴力,但激情的领域是超越善恶、无涉普世价值的,激情之路从来凶险无比;人生的磨灭多种多样,因激情而生毁灭不过是其中宿命性的一种。
而人与人之间不堪的东西,也远非这些洁净规整的心理学标签所能容纳。
《卡拉马佐夫兄弟》中,佐西马长老向德米特里深深一拜,因为他的情与欲都很强,是要尝尽人生之苦的。
秦可卿淫丧天香楼,宝玉则是古今天下第一淫人:溺于情而近乎淫,是一种悲剧性的精神强度。
激情、迷恋、着魔,作为一种不可控的存在状态、支配性的生命节奏,是我所能想象的最为极致的享乐与战栗。
写下这些,不过是我也这样入过迷。
7 ) 关于爱的叙述
本来只想写个看过的简短评论就,结果越写越长就索性改成长评,最后写题目的时候虽然为难与如何给一段毫无中心思想的短评写题目,但还是勉强取了一个名字,算是一句话对电影的概括吧,但其实强烈认为不能单纯用爱来描述两个人之间的关系,杨提到的统治与被统治,摧毁与重塑似乎更合适两个人之间的关系。
基于真实采访记录改编的电影,通过杨的叙述视角即非常主观(杨的感觉)又很客观(旁观者视角)这种关系很多面,很复杂,虽然杨说到他对同性依然渴望,对杜拉斯甚至有杀心,然而事实上他陪伴杜拉斯至死,杜拉斯死后他仍然从事着与之相关的工作,可能就像他说的自己不存在,杜拉斯创造了他吧。
电影拍的很棒,演员表演更是惊人,这样完全对话式单一场景的九十多分钟竟然让人可以不发困的看完,或许只有“浪漫又习惯深思”的法国人可以做到吧。
引号里对法国人的好的刻板印象正是因为许许多多这样优秀,具有实验性质的法国文艺作品带给了观者如此美好的“刻板印象”。
另外,电影色调很令人喜欢,湿冷环境中美丽房子里的温暖橘色灯光,蜜蜡色的家具,红色系的贵妃椅上蜷缩着的冷色调清瘦忧郁男主,如此画面,简简单单的就可以印在你的脑海里,在街头散步脑袋放空的时刻一下子就想起来,没有缘由,但会心生一种莫名的向往,向往那个故事那个时代还是那个国家,可能不会很清楚,但激起了些什么。
8 ) “我”想聊聊
3.5漫长的对话,文本式电影。
原型故事已奇情之至,按常规路数拍必吸睛无数,但影片弃大道择曲径通幽,以事后烟的平实叙事,引入间离与他者(记者)——①主体变成叙述者Yann (客体恢复成主体)聊的虽然是杜拉斯,但叙述的是“我”,主题是关系。
杜拉斯的引力过大,必须间离++方能有“我”的一方空间②Yann本是男同性恋者,在这段激情关系中处于权力下位,成为了真正的客体——话语权剥夺,被审视、被塑造,被支配,在女性处境(“女性是处境,而非性别”)③得以游刃有余地探讨幽微话题:激情性爱中的男女,恋爱权力关系中的男女(反转),异性恋与自恋,同性恋与自恋,扮演…话语与权力,爱与死…PS:Swann的演员功力窥斑见豹,细腻的语言及肢体节奏稳妥地驾驭住了大段台词(内在易碎气质亦加分)。
9 ) 聊聊杜拉斯
说实话是奔着阿劳德·斯万去看的,他在本片里呈现出的是与《坠楼审判的剖析》完全不同的样子。
笑称说他是2023年法国最性感律师,本片里呈现出来的一个被亲密关系裹挟的无助青年,更让人多了几分怜惜。
一部几乎都是对话的电影。
本片出彩的第一点便是对话本身,杜拉斯生前的最后一个情人所讲述的录音,由两位演员演绎出采访的过程,让当下的演员来重新“聊聊杜拉斯”。
我本来是很期待谁来演绎杜拉斯的,然而本片很巧妙地避免了这点。
在记者远去的视线里,别墅窗户里隐隐透出的背影便是了,而无正面镜头。
此外,在杨叙述杜拉斯如何把自己放进电影里时插入了电影拍摄的真实场景,我们真切地体会到杜拉斯对杨的掌控,更使本片向“伪纪录片”靠拢。
另一个有趣的点是本片对性爱的处理。
水彩画。
在记者躺在床上辗转难眠时,杨对二人性爱的描述在记者脑子浮现,是手绘的水彩画。
像是难以名状,只能隐隐出现在脑海中,在下一秒就要落荒而逃的高潮,仿佛做爱只是为了定格画中的那几个瞬间。
这样的处理方式也与杜拉斯本人对性的态度不谋而合。
总的来说,本片的意义更多在于“创意”,剧本与表演上的创意,至于在杜拉斯与杨的亲密关系探讨方面,只能说是浅尝则止。
10 ) 这段可怕的爱情也许没有更合适的电影形式可以将其准确表达
--- Yann Andrea,原名Yann Lemée,生于1952 年12 月24 日,死于2014 年7 月10 日。
1980年至1996年,以杜拉斯的伴侣身份进入了杜拉斯的生活和工作。
Yann Andrea是杜拉斯给他改的名字。
杜拉斯在遗嘱中委托他负责她的文学工作。
遗嘱赋予他的“文学执行者”角色,这是一个在法国法律中不存在的概念,在杨与杜拉斯儿子的诉讼纠纷中,对他身份和权利的裁定引发颇多议论。
可以简单的理解为杨是杜拉斯的精神继承者。
杨自己也是作家,他的所有书籍都围绕他与杜拉斯的关系展开,而且杜拉斯的写作风格对他影响很大。
外界普遍认为他的作品只是杜拉斯风格的复制品而非个人才华的展现。
他在死亡数日后被人在其寓所发现,之后被安葬在蒙帕纳斯公墓的杜拉斯墓穴中。
杜拉斯与杨的这段惊世骇俗的爱情故事,没人能讲清楚。
没人能够,甚至两位当事人自己都不能。
想象一下,如果杜拉斯活着时听了杨的这两盘录音带,她对于其中的细节会说什么。。。
虽然他们两人自己也未必完全认同对方所述为真,但整件事情,除了他们两位自己,谁也没有能力多说一句。
杨留下的这段采访,是在他有自杀企图之后,经杜拉斯首肯进行的。
采访内容在两位当事人死后才公诸于世。
杨坦诚的描绘了两人之间真挚也不堪的情感关系,今天看来,这也是杨,作为一个哲学系毕业的学生,一个不甚成功的作家,以自身经历为例,对爱与死,激情与存在所做的思考。
而这些话语,在真实意图和实际表达上,在讲述与聆听之间,在声音与影像里,又各自形成自己的真相,一份难能可贵的超文本。
杨的采访录音被他的姐姐逐字记录为文字,然后成书发表。
电影根据采访的文字稿改编而成。
导演曾在接受一个采访时说过她有意避免听录音带,她不想受杨的影响。
导演也许想避开杨的语音语调和语气,给自己留出一点点再创作空间。
而就是这已经非常狭小的再创作空间,导演发挥的精妙绝伦。
她以非常细致的巧思安排着声音,通过插入绘画、图像档案资料、过去场景重建、与绝非僵硬刻板的室内运动镜头相结合,完成了一部细腻生动,层次丰富的电影。
两位演员的表演绝对完美,而最成功的是暗渡陈仓的主题。
尽管高度忠实于采访内容,但这也是一部独立于杨的两盘录音带的电影,关于这部影片的主题,重要的不是杨说了什么,而是导演在其中要传达的信息。
言说是为了存在影片展现了一个在爱情中饱受摧残的男人形像。
杨与自己的欲望和杜拉斯的阴影作着不懈的斗争,他甚至走到了自杀的边缘,他迫切需要将他们的关系用语言表达出来。
她说:“我要毁灭你,重新创造你。。。
你什么都不是,你已经不存在了,你只能透过我来活。。。
只有我才是你的欲望。。。
““她拥有语言,于我而言,她是真理,她给我一切,我无法离开他。。。
” “她的存在是别人的十倍,面对她,别人的存在只能堕入虚无。。。
为了缓解这虚无,我需要说话,说说这些。。。
爱情中充斥着权力关系,有的不显见,有的很暴力,在杜拉斯那里,是一种更加可怕的肆意彰显的权力意志,随时准备吞噬反抗者。
杜拉斯拥有语言,杨被剥夺了语言,而此时此刻,面对被允许的采访,他暂时获得了言说的权利。
杨的话语说出最禁忌的爱的状态和欲望可能造成的奴役:“如果我想吃牛肉,而她想喝番茄汤,那么牛肉就上不了餐桌,我不能有除她以外任何欲望,她来规定我穿什么,吃什么,如何走路,我已经不存在了。
从洋葱到我的存在,我都让步了。。
她将我摆在女性位置上。。。。
我彻底放弃抵抗,取而代之的是一份超级保证。。。
“杨吐露心声自我剖析。
记者聚精会神地倾听。
这两盘录音带,既是对话也是证词。
这些话语是真实的,但似乎也是一种近乎表演性的陈述。
无论怎样,人的存在需要话语的佐证,杨的痛苦证明了言论解放的必要。
两位演员的表演非常出色,女记者浑身散发着友好善良、忠诚可信的气息,给人带来极大的安全感。
,她倾听,偶尔引导他深入探索表面之下的真相。
她谨慎的提问,带着克制。
渐渐的,她让我们看到男性的瓦解与这段爱情的运行机制。
男演员成功再现出杨这个备受折磨的男人脆弱而不稳定的精神状态。
尤其值得注意的是这段关系的独特性以及这部影片的吸引力多少来自这种受害者形象在社会中通常是为女性保留的,在人们固守的思维定势中,影片中的非典型男性形象需要呈现的足够令人信服,而更大的难题是采访这种形式无法给演员留出多大的表演空间, 然而通过对人物精湛的理解和把握,演员成功塑造了屏幕上弱小无助、美丽凄凉的杨·安德烈亚。
声音的运用严格忠实于采访录音很大程度上限制了导演,她不能改变采访的形态,也不能篡改杨的话语。
而言说如此重要,导演除了忠实于讲述者的陈述,也竭力突出自己想要强调的话语。
例如在第一天的采访结束后,记者回到自己家,她选择性的回放了一下录音带,在几次倒带之间,我们听到了一些显然是导演想让我们听到的关键词: 希望。。
失败。。
不。。
性交,我从未做过。。。
那是杨的希望,杨的失败,杨的抵抗,杨的拒绝。
在这场话语的瀑布中,导演截停了一些对她的再创作极为重要的话语。
导演还巧妙的利用声音让杜拉斯出席了采访。
在采访开始时,记者对杨说她进门后,在楼下见到杜拉斯,杜拉斯说要送咖啡上来,记者拒绝了,杨说他希望她不要上来,记者说,对,不要。
杜拉斯与杨的紧张关系就这样开门见山的显露出来。
在采访中间,我们还能听到一些噪音,是杜拉斯在楼下摔摔打打。。
然后,杜拉斯打电话过来,铃声持续且恼人。
杨抬起话筒,粗暴挂断。
杜拉斯时时刻刻存在着,在房子的某个地方,在记者的提问中,在杨的回答中。
阴魂不散的杜拉斯,势不可挡、令人窒息,她的这种不在场的在场骚扰着整部电影。
不过不知道是出于什么考虑,导演还是让她出现了一点点。
第一天的采访结束于傍晚6点15分,记者离开,男人下楼,透过窗户,导演让我们看到了杜拉斯,在一楼房间的角落里,男人迎向她走去,那个颇有辨识度的矮小臃肿的身体,穿着白色毛衣。。。
(可怕的杜拉斯,不知道让她仅仅是可闻不可见还是这样隐约的浮现一点点更让人觉得惊悚。。。
)图像的组织在采访中,记者发现杨总是使用过去时,她提醒了他。
虽是发端于过去,但事件并未结束。
杨的一些回忆被导演以闪回的方式再现,但闪回相当于影像的过去时,既然导演着重重现了记者对杨关于时态的提醒,导演本人自然也想要遵守语法的规则。
所以当画面重建过去的场景时,导演让此时的杨的声音继续,而彼时的杨则说着同样的话语,杨说着曾经说过的话,词语错落重叠,两个时空中,杨同时身处过去与现在。
是他,主动开启了这一切,过去并未过去,现在只是那个开端的延续。
杜拉斯纪录片档案图像的插入是完全属于电影的,也许是为了将杨所讲述的某些内容与杜拉斯形成对话。
在第一天的采访中,杨讲述了自己与杜拉斯的第一次相见以及第二次见面后他们在一起度过的那段时光,杜拉斯不可思议的热情,以及满足杜拉斯给他带来的震撼,他的恐惧,被激情挟裹的惶惑。
导演插入的档案资料则是杜拉斯在用自己的语言表达了她对那最初的时光的感受,两个人的感受,完全不同。
除了杜拉斯的纪录片的影像资料的插入,其他影像资料的使用还有《印度之歌》电影片段,对于杨和杜拉斯,《印度之歌》之后,再无电影,癫狂与死亡,没有什么比这部电影用来做他们俩的脚注更合适的了。
影片还有一个片段脱离了杨的独白,即在两天采访之间的晚上。
记者步行回到自己家中,当天的采访令她难以平静,她躺在床上想象着,杜拉斯和杨的亲密动作由一系列水粉画呈现出来,这些内容应该并非空穴来风,而是在采访中被杨有所提及。
导演拒绝以语词再现而是选择了绘画的方式来呈现,疏远的距离,明显的第三方的视角,记者将自己从杨的文本中抽离出来,从自己的角度思索这段复杂独特,充满悖论的关系。
这场冗长采访的录制并不是纪录片,而是对当年的那场采访的虚构重建。
杨的痛苦独白常常令人窒息,在他说,她听,她提问,他回答的单调与沉重中,导演精巧的构思,借用以上声音与画面的电影手法让影片变得流动起来,层次也愈加丰富。
导演在忠实于原话语的规则之下又勇敢的打破电影的类型框架,真的是一部充满创意的作品。
杨说了他想说的,电影另有主题要言说她把我放在女性的位置上。。
她把我当作女人。。。
他说。
杨在描绘他与杜拉斯的关系时用到“统治”与“被统治”这个词,女记者提醒他:你想说的是“臣服”。。。
男人承认又反驳道:我不喜欢这个词,不如说“接受”,我接受了她的一切,正如她说:接受或离开。。。
导演就是从这些词语中构建了同步于杨的另一种言说,爱情运作机制中始终存在着对他人的控制,有的以温和的形式,有的以暴力的形式。
为了满足对方而牺牲自己的个性,同意对方按照他或她的品味重新塑造我们。
在爱与欲望的游戏中一方逐渐成为另一方的从属物、创造物。
这残酷而危险的游戏也许没人能达到杜拉斯与杨的程度。
导演在一篇文章中说道:作为一名女性和女权主义者,对我来说有趣的是,在这个爱情故事里,我们看到了一种堪称典范的对服从的描述。
因为对于几个世纪以来遭受压迫的女性来说,说出她们所受的压迫是非常困难的。
扬是一个处于非常弱势地位的人,但由于他有男人的文化,他能够非常准确地说出发生在他身上的事情。
这个描述很有趣,因为它是对方做出的。
杨说,他在第一次见到杜拉斯时,口袋里装了她的一本书:《毁灭,她说》,这时我们听到,记者出声重复了书名:《毁灭,她说》,我们先是听到记者的声音,然后镜头从杨的身上摇到记者身上,我们看到记者在记事本上写下了书名。。。
这看似正常而不经意的一个采访动作,却暗藏玄机般道出了杨与杜拉斯情爱关系的核心。
杜拉斯是作家、导演和思想家,她是杰出的女性,年长且经验丰富,她跻身于上流社会,是风云人物,她的文化成就,以及她的自恋性格让她处于强势地位。
杨被这种成就与强大所吸引,我们不用怀疑,他是爱她的,因崇拜而来的爱,她是高高在上的神,渺小爱上崇高,想将自己的名字写在神的名字旁边。
他爱上她,想参与她的不朽。
杜拉斯绝对是暴虐的,她重新命名了他,她重新塑造了他。
在这场吞噬和消耗的爱情中,杨脆弱又顽强的抵抗着。
他在清醒而痛苦的同意下放弃了自己的自由意志。
他接受不对称的关系,屈服于杜拉斯的欲望与爱。
但他仍希望保留自己的存在,如果自己不存在了,参与杜拉斯的不朽又有多大的吸引力呢。
于是妥协,让步,离开,回归,自杀,他将各种手法用尽。
而最有力的抵抗也许是他声称自己是同性恋。
关于自己的性取向,杨给出了时有矛盾也颇令人困惑的话语。
他说,同性恋。。。
是一种缺乏,爱的缺乏,缺乏拥有/属于某个人的感觉。。。
感觉不到自己活着,身份的缺乏,。。
于是,男性的小树林,杨逃跑的地方。
因为那里有一个群体,有他们的符号和密语,是杜拉斯无法抵达的一片新大陆。
杜拉斯侮辱了他的性取向,将其形容为野蛮。
杜拉斯说同性恋是死亡,并将其写入书中,让世人广为流传。
她采取一项消除政策:这样就不再有性偏好。
她叫我断了一切欲望,她意识到了她必须认真对待我的同性欲望,她说只有她是我的欲望。
我对她说过她不会熄灭我的同性欲望。。
在这性别的流转、取消、趋同、泯灭的战争中,杨并不全然是一个受害者、无辜者:他思考并接受(服从)。
他似乎从来没有迷失过,就算是透过杜拉斯来活,他也始终用她的眼睛盯着自己,他是她欲望的对象。
他并不否认这份爱给他带来的所有好处。
他认为自己很荣幸,因为他得到了他崇拜的女人的关注,因为他成为了她的欲望的中心。
他在这一切中看到了进入他所崇拜的独特宇宙的特权,这保证了他的不朽,他们互相书写,专属于他们两人的文学与肉体的关系,被印刷,被出版,被关注,被议论,被诅咒,被崇拜。
这也许是人类所能达到的最高体验。
也只有他,就是他,能与杜拉斯一起在矛盾的建构和破坏之中互相为对方增添传奇。
“我与她的爱,是全部,是永恒。。。
激情的真相,爱的真相,就是死亡,是摧毁一切的爱,没有摧毁,没有死亡,就不是爱。。。
我无法想象她死后的自己。。。
她就是美好本身,我无法不爱她。。。
”在影片快结尾时,消瘦憔悴的美人,坐在他东方风情的床榻上,在蜜色的灯光下,问记者:当我讲她对我的爱的时候,我讲的是我对她的爱,是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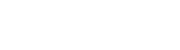





















我没有穿某件衬衫的权利,却在树丛里与某个男人鬼混。她拥有将我毁灭重造的能力,却在用阴性跟我对话。杜拉斯仿佛才八岁而我已经八十岁垂垂老矣,人生是从何时开始转向,第一次阅读她的文字,第一次拿到她的地址,第一次与她的性爱?爱情又是何时开始转向,或许从一开始我们就是两盘不会被取回的磁带。
比较有印象的是:扬房间的东方饰品摆件,女记者房子的壁炉和装潢,以及法国别墅区的灯,树,色彩审美,扬对自己在关系中同性恋和阴性身份的分析。加入的性爱漫画能直观地让人意识到扬和杜拉斯发生关系的画面,皮肤的皱纹,扬的性感,弥补无法拍摄的不足。但是跟这么多人一起看还是觉得尴尬。整体上觉得电影传达的信息不足,一个采访或者电视节目就足够了,不需要法国张震来记这么多台词。
内容如其名 像平静的水面 或许对杜拉斯本人更有了解的人看起来会有更不同的感受?
SIFF 2024 第三场,FANCL艺术中心(艺海剧院),楼下8排,稍微有点靠前,需要微微仰头。观影过程一言难尽,如果隔壁不是狐臭且频繁看手机的男人就好了…
电影还是纪录片 不知所云
很特殊的观影,整部都是以对话组接的镜头,没有一丝视听塑造,但此片却介于剧情与记录片的中间地带,让我们了解到了杜拉斯的另一面。当然,此片有意思的是男主是一位同性恋,但作为杜拉斯的粉丝,也能对杜拉斯产生爱意,当然这种情感展现的十分微妙。而此所要探讨的情感或许也是在此片的真正价值所在。
全程对话的密集程度枪林弹雨般往下掉落,看到后程无法穿插任何想法,像拉着紧凑的网不断接住繁冗的信息,同时充当男主负面情绪收割机。美感从话题引入但开口三言两语遽然了解欲全无,越来越困倦,这一个半小时,何尝不是一种domination
没有大起大落的剧情,就是女作家和男主的谈话和回忆,点一根烟思绪萦绕,观众被谈话的内容吸引,杜拉斯所有的强势等等!有时越简单的电影越耐人寻味,“这里同样暗藏着秘密,午夜梦回的暧昧缠绕,身形几乎消隐匆匆略过”,喜欢这样的文字!也喜欢片中的光线,小屋,炉内的篝火,窗外,水塘边摇曳的树叶,法国人真是太有意境了!
全程略沉闷,状态表演得挺好的,swann完全beta男专业户
在第一次对谈结束后,随着女记者的想象或者梦,在第二次对谈二者的主客体发生了一个变化,也由Yann的讲述变成了女记者去判断的一个过程,这儿语言的真实性被置于怀疑中,杜拉斯也开始如她电影中的那些女主角一样成为了幽灵。
杜拉斯对世界的爱由语言的自由组成,对恋人的爱则由语言的绑架组成。一部全然奉献给语言,任由语言与回忆的影像、想象的影像、表演的影像合谋的电影。后半部分在男人像个小孩似的控诉杜拉斯对自己的控制时,特别像一部女性恐怖电影。前半部分则成为文学沙龙,利用法语特有的曼妙,去诠释语言悠长螺旋的历史。电影本身并不针对杜拉斯,更针对表达本身。
女作家杜拉斯和她的恋人,以恋人的角度说出杜拉斯对他的改变,男同性恋和女性,支配与被支配,扭曲,疯狂,略带病态的爱,一个半小时的电影,几乎全部是在室内的对话,但是完全不无聊,对话被情绪和人物关系填满,被杜拉斯塑造改变支配的男人,扭曲的爱与恨,斯万·阿劳德很适合这种带有脆弱气质的男性。评分:8.0/10。
自下而上的虚构与想象 完成了对杜拉斯的精神世界的一次完美建造
siff26/我以为讲的是杜拉斯的生平没想到讲述的是杜拉斯晚年的一段畸形恋情,“她扮演着男人的角色,她负责交谈提议为我发言,她下命令,她做主人”“她将我摆在女性角色上”。当坠楼的审判里的丈夫走进现实,我不认为杨对杜拉斯有丝毫的爱意,这些自述虚假无比。
我可得去读读原文,这语言太精妙了。几乎是完全颠倒了性别刻板印象。没想到导演来了,她说采访者回家后的感受就是我们所有人听录音后所体验的。
最近看的两部法国电影都好淡…还没特别习惯这种表现形式 当然这部比火锅的引发的思考要多 形式上也更极简了 短短两天一夜 穿插影像片段这个爱情故事本身就极具话题度 话题的展开非常具有法国特色——关注人对于这个身份的认同 对于爱、性和两性的看法 因艺术结缘的恋人“地位”如何 以及他如何看待自己的存在 对杜拉斯影像的选择丝毫不留情面 以至于我认为她是个控制欲十足的mean老太太 女人可以坏 但何不坏得迷人
《我們談談莒哈絲》的採訪背景1982年,當時莒哈絲已年屆70,而楊.安德烈不過30出頭。兩人透過莒哈絲的電影《印度之歌》(Indie Song)而結識。在長達多年的書信往來後,兩人展開了短暫的同居。綜所皆知,莒哈絲的經典小說《情人》(L’Amant 1984),即是由楊.安德烈整理而成。他同時擔任了莒哈絲的電影演員、愛人以及口述著作代筆。而他的「同性」性向,和莒哈絲的忘年之交,無疑為小說《情人》提供了最佳的題材。《我們談談莒哈絲》(Je voudrais parler de Duras)直到2016年才出版,當中也包括了「電影筆記」記者米榭.芒索於莒哈絲家中對楊.安德烈所進行的採訪內容;這些場景成為了導演克萊兒.西蒙重新形塑與捕捉的對象。史旺.亞勞德飾演的楊.安德烈,為了符合在莒哈絲掌控下的生活樣貌。
一个活在杜拉斯阴影下的,被杜拉斯塑造改变支配的男人,扭曲的爱与恨,但无法剥离,一种病态共生关系。斯万·阿劳德太好了,细微而精准的面部表情变化支撑起了几乎全部是对话的电影。
混合模糊的叙述,意不在重构杜拉斯,而是拾起时间碎片
充满个性也有着不同效用的另类传记式致敬,开场之后展开的对谈、偶尔的吞云吐雾以及被温暖包裹着的玻璃房,它让人坐定可以去倾听各种各样的故事。那些真相,那些个人化的叙述,在追问与思索之间来回游弋…这样的设置与过程让人舒服,对各种影像资料的穿插使用作为间接的打断抑或一种互文的安排来进行调剂。我想聊聊都拉斯,我想(更)读透都拉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