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子》剧情介绍
《日子》长篇影评
1 ) 日子
今天我感到非常沮喪和失望 我倒沒有太過憤怒 因為這樣的事總會到來 只是早或晚 而這回來的過早 早得令人感到詫異 令人不知所措 對人性感到一股的寒意不久前帶去柏林參賽的《日子》我的製片因應部份媒體及片商的要求 把影片的樣片寄到某些人士手中 我們是多麼的信任每一個人對著作權的重視 但事情就發生了 有人把樣片資源流了出來 非常非常令人震驚 以後我們還要相信什麼 人和人之間還會有信任嗎這事傷了我們的權益 傷了我們的作品 也傷了我們的心如果你是我的影迷 或是電影的愛好者 我懇求你不要像那位傷我的人那樣傷我 那樣的傷一部作品 認真的拒絕在這情況下看《日子》也幫忙我阻斷所有的輸送 甚至幫我查到發放的原兇也許我永遠也查不到是誰 但我深信人在做 天在看 你知 天知 只是時候未到而已蔡明亮
2 ) 旅馆才是我们与恋人记忆最深的地方
对不住了蔡导,我上不了柏林也买不到正版,但我还是看了,而且还不要脸地觉得挺好看。
每个人看到的都不一样,越是朴素自由的电影越是开放。
许多人都觉得它不好,确实它比起蔡的其他电影更松弛。
一般导演到这个年纪都开始搞玩票之作,更不着力也更讨巧抑或更找骂之作。
但今日的我也已更松弛。
我们都看了十部蔡明亮,又何缺第十一部?
导演说这第十一部是上天给他的意外礼物,所以他会继续拍,我想也是给所有人的礼物,而我也会继续看(偷偷地看)。
所以是要很惭愧地说声谢谢。
《日子》我看了两遍。
第一遍时,没有耐心看满两个多小时,前面人物没有相遇,就跳着看一看。
得失心太重,知道他们在干嘛,知道镜头动都不动,就没有兴趣随它静止,而是在心中像语文课写段落大意那样记上一笔:他干了这个,他干了那个。
如此一来,电影也就失去意义。
我看大多数人也和我一样。
比如,看着李康生发呆时,我的思绪总会飞跑,我会想我并没有真的进入他,跟着他发呆,而是在评判他表情的变化,评判电影,评判我自己。
他是在面对他自己,还是在面对观众?
我是在面对电影,面对他,还是面对我自己?
我唯有面对自己,才能面对面对自己的李康生,然而这又一再使我滑出电影。
我只能在停顿和跳过中,在自己的观影节奏中,保持电影的节奏,而不被它催眠或被思绪吞没。
直到旅馆,直到他们相遇。
该发生的都发生,一切都随之改变。
所有各自的平常的行动都有了不同的意义,被他们曾经共有的时刻照亮。
电影在这里真正开始,并给我无限的感动。
第二天我又看了一遍。
时间有什么好珍贵呢?
我们拥有过的全部时间,正是我们浪费的那些。
我不再计算镜头还要多久才结束,然后我发现它们远没有我们想象的那么长。
电影最有意思的地方,从来在于如何处理与时间的关系。
电影因捏造时间而有魔力。
而在蔡明亮的电影中,时间被“拉长”,趋近于真实。
这真实有时比“实际”的时间更加难以忍受。
真实不同于实际,在实际的生活中,我们其实很少真实地面对自己,即便在独处时,因为真实会带来比他者更急切的危险。
哪怕写作,也是人同时面对自我和逃避自我,是人和自己做游戏,这自己已是房间中被创造出的另一个人。
日子不是河流,日子也不是洞,日子就是《日子》,它东升西落。
在这里,干脆放弃情节的描画,放弃电影的工业之手。
于是摄影机有了自己的眼睛,我们看到不完美但由自然巧妙合成的世界。
它看到什么,我们就看到什么。
我们看到什么,那就是什么。
我们也听,静静地听。
所以再没有哪部电影,包括蔡明亮的其他电影,给我这样的感动。
李康生走进旅馆的房间。
此后在这个房间里,始终没有刻意拍什么特写。
正是这样,我们始终看到那房间。
那房间我们实在熟悉不过——此时你又会想起谁?
李康生把被子的角一点点抽出来,再叠好,就放到椅子上,并不拿到摄影机之外。
平常的令人生厌的阳光从窗口照进来。
他点上一支烟,在手机上发消息,再坐下。
那些动作太平常,太放松,我甚至有偷窥感,后来也就一直有。
亚侬的脸很普通,一张可以获得的脸。
他的手慢慢在他的每一寸皮肤上划过。
在最后的时刻,他才寻找他的吻。
迅疾的一刻。
他给他洗澡,擦洗身体,把液体冲刷掉。
穿上衣服,他留他。
从包里把小小的音乐盒拿出来。
他有点惊讶,笑着,一点一点摇,十分仔细地听。
李康生也坐在床沿,眼睛看向墙壁,抖抖手里的烟。
没有什么语言,过了很久。
是要久些,也够久了。
他走了。
过一会,他还是追了出去。
旅馆的灯熄灭。
它什么也不知道,不记得。
像我们每一次和情人开过的房间那样。
只要走出去,我们很快就会失去联系。
世界熙熙攘攘,又安安静静,循规蹈矩。
夜晚像一张大床。
摄影机在街对面,中间车来车往。
无数的镜头都像这样,靠我们的目光来找寻。
你要盯住,否则就不再能看见。
李康生又拿出手机,拍视频不知道给谁看。
手机这东西,在蔡明亮的电影里,其实不怎么出现。
手机在今天的意味太明显,太干涩。
它使孤独有了新的层次,新的高度。
它使人未曾得到彼处,先就失去了此处。
但为什么不能拍呢?
这就是我们今天的现实。
在夜晚的公交车站,他独自坐下来。
那是路口,没有人看他,不断有人走过。
那是任何一个异乡的任何一个公交车站。
他看向他们,他不看向任何一个人。
他把音乐盒又拿出来,一个人慢慢地听。
是卓别林的作曲,李香兰唱过的《心曲》,《黑眼圈》里也出现过。
比在旅馆里时更慢,一个一个音符,小心地踏出来,他不知看向何处。
广告牌在身后发出幽幽的亘古不变的光,城市很安定,人们都有家可归。
黑夜里,没人关心这路边的音乐盒里流出什么样的魔法。
过了很久,大概有一支歌那么久。
他拾起包,重新走入这人群,像黑夜消失在黑夜中。
3 ) 一个老0在镜头前趴了两个小时
如题,全剧终(以下都是凑字:镜头一:老0坐着看雨10分钟;镜头二:按摩鸡蹲那洗菜10分钟;镜头三:按摩鸡做饭烧开水10分钟;镜头四:老0后背熏艾灸10分钟;镜头五:按摩鸡给老0按摩背面10分钟;镜头六:按摩鸡给老0按摩正面10分钟;镜头七:按摩鸡坐公交车站牌下10分钟;没了,够140字了吧)
4 ) 对不起!
虽然说不是蔡明亮导演的老影迷,但是在蔡导的新片《日子》曝光预告之后我便开始期待。
这几年陆陆续续看完了蔡导所有的电影长片。
我永远无法忘记当初第一次看蔡导的电影,看《爱情万岁》的那个下午,曾经无数的少年时代的日子全然随着那些安静孤独的画面产生情绪倒带,当所有的镜头最后停留在一个女人的一张脸上,一张哭泣的脸上的时候,似乎除了哭泣声外全世界都安静了,只剩我的心脏和哭声虬结在一起。
从那之后,我就爱上了蔡导的电影,并且一发不可收拾想要找到他所有的影片看,然而,正规的平台上只有《爱情万岁》,《青少年哪吒》和《郊游》,仅仅这三部也全都有不少的删减。
平日里无论是对盗版文艺片还是盗版书籍和音乐有很强抵触心理的我,怎么也按耐不住对蔡导电影的热爱,一部又一部从极少的盗版片源中找到了仅有的能下载的链接,即使画质再差也一点法子没有地看完了。
当《日子》发布预告片可想而知我有多么期待和兴奋了,然而同时我也知道这种题材的电影很可能是无法在内地上映的。
于是我便只能等,等到在柏林上映之后希望能够看到片源,毕竟实在没有经济条件去柏林观看首映。
首映过后,我心心念念在豆瓣开了个讨论,自然是希望有天有人能够在讨论下面贴一个片源链接。
于是我每次上豆瓣都会点进去看看。
直到前天点进去,看到有人发出了片源,我什么也没想便迫不及待保存了下来。
在此我说明,我并不清楚那是内鬼散播的资源。
当然不管是谁散播的盗版片源都是在我开的讨论区下面传播出去的,若是我不开那个讨论或许就不会有人把链接贴到豆瓣上。
身为蔡导的影迷,我衷心道歉。
我也绝不会把手中的片源传播给下一个人。
希望蔡导能够早日找到盗版的源头,也希望未来能有更多的人尽量抵制盗版的传播,无论电影还是音乐和书籍!
2020.4.8.下午
5 ) 柏林专访蔡明亮:告别语言,种下四年影像它自会长出寂寞和思念
《日子》仅借由一种对影像记录最纯粹的冲动——它一经给出就是具体躯体,具体物件,具体动作,具体情境,在时间潮汐式的来回运动里,影像自发生长出了自己的“故事”,长出了自己的寂寞、欲望和热烈。
《日子》是蔡明亮在《郊游》之后,时隔七年第一部剧情长片,也是柏林70周年唯一一部入围主竞赛的华语电影。
其实这样的表述实在太不够确切,首先这部电影并没有出现一句“台词”,说是华语,不如说是华人导演和演员;其次,在过去七年里,蔡明亮从未停止过创作。
无论是装置还是VR,无论是剧场还是咖啡;第三,因为《日子》并没有任何剧本,你甚至也可以说他是纪录片,其中大量影像只是对李康生治病以及老挝男孩亚侬在泰国打工的真实记录。
这些日常生活的影像断断续续在四年之间在世界各地被蔡明亮收集着,没有特别的目的,直到有一天他决定让这两个不同生活中的男主角交汇在一起,直到有一刻两个人的日子变成了一种日子,都市里寂寞的两个人终于坐在了一起,伴着车水马龙的喧嚣,共食一餐饭。
在观看蔡明亮新片时,我试图把电影的每一场戏都大致做一个笔记。
众所周知,蔡明亮的电影以长镜头为主,每个镜头内人物运动通常也十分简单甚至近乎于无。
但我很快就意识到这几乎是一件不可能的任务,或者更准确说,这是一项愚蠢的工作。
在黑暗中,我的笔头落入某种文字所预设的陷阱。
如果仅仅把《日子》还原为场景中人物的动作,我所能记录下的极其稀薄信息又和蔡明亮电影有什么关系呢?
那些我面对着饱满影像所滋生出的情感,那些影像中的人与物自身所酝酿的巨大情绪和气息,通通都从我的纸面上溜走,不仅无法凝练成一份说明——这些贫乏的文字甚至无助于我唤起观影时记忆。
“语言其实是有点危险的。
”在蔡明亮提醒我之前,我又何尝不知道这一点呢?
但或许这种“健忘”才是语言真正危险之处,因为我们实在太习惯于使用语言,太过于依赖建构在语言之上的,这个泾渭分明,可供我们清晰交流和行动的世界。
而影像则是前语言的,影像也是有厚度——这些充盈着身体细节,日常动作,自然景观的沉默世界在目光绵延的回转中酝酿着个体丰富的记忆,撬动着感知深处的欲念和思绪。
而蔡明亮影像正是生发于这鸿蒙暧昧的原始直觉中。
《日子》影像结构是从早到晚再到清晨的完整的一天,观众不仅很难察觉到这些影像跨度长达四年,甚至很难区分出他们是在曼谷、台北、香港等不同地方收集的。
这样低成本的制作方式已近乎电影拍摄的极限,在几个人手工作坊式的“漫无目的”的日常影像积蓄中,电影回归了其具体主义的本质,它完全反对编剧的概念,也回避了概念和意图前置的驱使力,仅借由一种对影像记录最纯粹的冲动——它一经给出就是具体躯体,具体物件,具体动作,具体情境,在时间潮汐式的来回运动里,影像自发生长出了自己的“故事”,长出了自己的寂寞、欲望和热烈。
深焦:第一个问题,我很好奇,为什么电影开头要专门用字幕强调这是一部没有对话电影。
因为事实上您的电影,一直话很少。
蔡明亮:因为观众,特别是亚洲观众,一般习惯听到对话就要有字幕。
如果有对话但没有字幕,他们可能就会觉得是放映出了问题。
所以我只是为了让观众踏实,提前告诉他们不会有任何字幕了。
深焦:其实语言对于您的电影,本来就不重要,您的作品一直是一种纯粹的影像。
蔡明亮:是的。
你知道《黑眼圈》就对话特别少。
但我记得,有一段李康生遇到马来人在变魔术,马来人在表演的同时也在互相说话,那一段本来也是没有字幕的。
但欧洲片方就一定要求做字幕,因为希望能让观众“看懂”。
但事实上我的看法就是,其实你一定看得懂,你只是听不懂他们在讲什么而已。
(有了字幕)反而让观影回到一个更现实的概念里去。
《黑眼圈》(2006)深焦:您个人对语言是一个什么态度?
蔡明亮:越简单越好,有些东西是语言无法表达的。
打个比方,你知道我是一个不准备的人,我做演讲,常常就根据当下感觉讲,有时候讲完就觉得今天讲得不好,就有些后悔,怕观众误会了我的意思,所以你看语言其实是有点危险。
语言也没有那么重要。
深焦:回到片子本身。
您自己也说这部片子没有剧本,您从一开始也分不清是在做纪录片还是剧情片。
观众应该都注意到,应该是第17个镜头,小康治疗过程中头发烧了起来,您的声音也出现在了电影里。
蔡明亮:是是是。
因为有很多画面在拍的时候,当时并不知道最后会变成一个电影,只是记录下来,只是一个机会。
比如这个场景,我们知道这个师傅是这样治疗的,所以就提前和他联系,他电话里同意我们去拍摄,我们就去拍了,拍来干嘛,我们也不知道。
比如我拍亚侬做饭,我也不是特别清楚,最后会变成《日子》这样一个电影。
我前前后后去拍了好几次,但也并不清楚最后会和李康生看病这个事情放在一起,是慢慢慢慢才开始把这两个事情放在一起。
《日子》中老挝劳工亚侬深焦:所以我还是得问,是什么时候,您决定把这些东西都放在一起做成一个电影。
蔡明亮:我已经忘记了。
是后来有一天,我和我的剪辑师说,我们把这些东西剪剪看。
深焦:那大概是什么时候的事情?
蔡明亮:是我们拍旅馆镜头之前,我们剪了一段时间之后,才去再找一些东西来拍。
深焦:哪些镜头是为了这个电影专门拍的吗?
我能具体知道吗?
蔡明亮:哈(大笑),后面旅馆部分都已经是专门拍的。
因为那时候已经开始在找钱,一些后期基金。
但前面都是我自己公司的钱,前前后后三、四年,同一个摄影师拍的,很多也都没有剪进来,也有我在的,也有记录小康生病在欧洲的,画面都很好看。
但后面再做剪辑的时候,有点去芜存菁,变成一个这样简单的结构,它本来还有更复杂的结构。
是我自己剪剪、停停、看看,觉得说还是要把它当成一个作品来处理,不要那么任性。
李康生和亚侬,终在影像世界里相遇深焦:我留意到这次您的摄影和剪辑都是张钟元,这种情况在一般剧组是很少见的。
蔡明亮:他最早其实是我的一个粉丝。
他高中就看我的电影,所以算是一个……“影痴”,观影经验很丰富。
在《郊游》里,他是侧拍,做纪录片,我突然认出他。
后来我拍东西或者剧场作品就经常找他来做侧拍或者剧照,逐渐我就很信任他,而且他是一个在影像很有天分的小孩,于是我就开始和他合作。
因为这个作品零零碎碎拍了四年,都是他在拍,因为他不是一个正式摄影师,时间上就比较空,年轻人机动性又很强,所以我要他来,他就随时来。
剪辑也就是他带东西到我家,用电脑剪,所以我就可以用更多的时间,少一点的钱来做这个作品。
深焦:素材是不是特别多?
剪了多久?
蔡明亮:很长,超过半年以上,零零碎碎的剪。
我没有乱拍,素材没有说多到不行,虽然一些素材没有剪进来,但剪进来的素材都带有我的思考。
深焦:片名叫《日子》嘛,所以现在结构感觉就是一天的事情,从早上到夜晚,再到第二天清晨小康醒过来。
但最后一个镜头出乎我的意料,我也不知道亚侬在等车?
或者是?
蔡明亮:不知道(大笑),人流走过来也走过去,不知道。
深焦:我甚至也不知道是日出前,还是日落后。
为什么这么处理结尾?
蔡明亮:你这样问也难倒我了,为什么这么处理,我就这么处理(大笑)……这个电影很明显就是在关照两个人,两个躯体。
一个年轻的,一个年长的,一个生病的,一个被困住的,或者说两个人都被困住。
一个是被病情,另一个是被他的身份或者环境困住,住在都市里的两个人,各奔东西。
我觉得这是我的一个关照,看看这个年长的,再看看这个小孩,可能是不经意的一个礼物,其实是种下了一些东西,也长出了一些东西,长出了一些情绪,长出了一些思念,长出了一些寂寞。
深焦:所以除了小康,这次亚侬角色特别重要。
您是在什么样机缘下认识了他?
蔡明亮:我是大概三年前,去泰国旅行,在一个美食中心遇到他。
他是一个厨师,在外面休息,我在吃他做的东西,就和他聊天,就是一种感觉,觉得很有意思,样子也很好看,也没有当场拍照片,只是留了他的电话,后来有通讯就变成了朋友。
深焦:所以和当年遇到小康……蔡明亮:对,很像。
但其实找小康,我还有目的要找一个演员。
但遇到他,我没有任何目的,就是交朋友。
后来我们用wechat视频就熟了,看到他在宿舍里做的一些事情,就很有感觉。
就问能不能来拍他。
深焦:所以他洗菜做饭就是他自己住的地方?
蔡明亮:是的,就是当时他在泰国住的地方。
他们换工作,换住处,生活很飘忽不定,他在泰国已经呆了六、七年了。
深焦:他做饭拍得很好看,是一个特别低机位,您是怎么确定一个空间里,镜头的位置?
蔡明亮:其实我们非常被限制,我拍电影全部镜头的位置都特别简单,该怎么摆就怎么摆,因为没地方摆,没地方打灯,我们都是没有用灯具,只是用一些很小光线补一点光,让画面不要太“毛”(糙)。
因为这些空间浴室、他的房间,都没地方藏东西、挂东西。
我基本上觉得摄影机只要去处理构图、拍摄对象基本的美感就可以。
比如,小康烫到头发那场戏,都是没有设计的,我们去拍小康治病,医生是不会等你的,这个治疗半个小时,我们就换了几个机位,没有太设计,只是要看清楚而已。
而且治疗发生意外,也不是设计的,就是真的这样发生了,那个医生还说几乎不发生这样的意外。
所以我也很不好意思拍到他烫到人这样事情(笑)。
不需要去专门分析研究我的镜头怎么摆。
其实我拍电影就是这样,没有什么设计,拍到什么就是什么。
深焦:《日子》一个很有意思的地方就是,好像这就是一个一天的故事,但其实在很多地方拍,我也分不清在哪里。
当时看电影时候,鹿特丹选片人谢枫坐在我边上,就悄悄问我,这个是不是香港,那个是不是……我知道肯定有曼谷,也有香港?
蔡明亮:对,有香港,有曼谷,还有台北,本来还有欧洲的,后来剪掉了。
但这个作品其实很单纯就是在观看两个身体,就是靠着素材来思考。
即便我后来再拍,我也没有思考,我也没有写下来,也没有告诉出钱的公司后面要怎么发展,他们不知道,我也不知道。
我只知道后面我要让他们两个人碰在一起,或者说在同一个空间里出现,不一定要发生什么事情。
当时有很多想法,但我很害怕又回到那种编剧的概念。
但你知道这很难免,当你有一个叙事的时候,就是一个编剧的概念,但这个编剧不是靠写出来的,也不是靠谈出来的,它就是在拍的进行中,一直发展一直发展。
深焦:最后你安排一个情欲的按摩让他们交汇。
蔡明亮:很原始。
其实对于很多人,这都是生活的一部分,去治疗,去按摩,然后按摩中发生一些性行为,这都是很普通,很多人都经历过的事情。
亚侬、蔡明亮、李康生在柏林首映红毯上深焦:所以“性”在这里很重要。
蔡明亮:当然很重要。
人与人相处,最后留下一些什么东西,是什么?
这不是一个故事片,我们不用说的很明白。
正因为它不是故事片,它说的不是很明白,所以它很真实,思念很真实,寂寞也很真实,不一定要完成。
生活普遍就是这样,没有事情被完成,完成都是编剧在完成,或者电影在完成。
我不觉得需要完成,所以我现在最感兴趣就是拍没头没脑的电影(笑)。
我们长期都被电影的完整性……所“洗脑”,洗到我们习惯、束缚了,看不到更多东西,看到的可能都是假的东西。
我觉得通常真实的都是没有完成的,来不及完成的,或者不会完成的,所以人生才会有感触。
深焦:您现在拍电影已经简化到几个人,已经是一种最原始,最手工方式。
蔡明亮:非常简单的方式,我很害怕假装在拍电影的样子,一大堆人,谁有助理什么,其实是非常影响思考的。
我一直想脱离这种状态,除非逼不得已,有些项目是需要一个团队,但你不是每场戏都需要。
我已经非常厌恶工业的方式,但以后会不会回到那样一种方式,也不一定,要看接下来要拍什么。
《日子》正好可以这样拍,我就这样拍下来了。
其实,我也在找我自己(做电影)的方式。
创作不是说你知道然后你去做,反而通常你都不是很清楚,隐隐约约觉得说想要这么做一个电影,可不可能。
所以这样就会有一个起头,起头是最难的。
这个想法最好就不要通过剧本来弄了,我们可能可以通过造型,比如我们可以和一个艺术家合作,通过做一个空间的造型或者一个演出来完成一个电影。
蔡明亮:你那天看电影,有没有什么特别触动?
深焦:我最喜欢的就是海报选的那场戏。
这场戏之前铺垫真的很妙,小康已经把亚侬送走了。
但在房间门口又犹豫了一下,最后还是追上去。
然后镜头远远捕捉到两个本来都很寂寞的人很安然在马路对面的小店里一起吃东西。
蔡明亮:哈(笑)。
这里面其实有很好玩的事。
本来他们是要一起出去的。
但我们其实没有沟通好,所以亚侬不知道要一起出去,到了门口就直接说了byebye就走了,(小康就傻了),自己就让他走了。
我自己就觉得很动人。
深焦:所以他们一起吃东西那场戏是偷拍吗?
蔡明亮:也没有偷拍,其实也算偷拍。
老板娘他们都知道我们在拍,但不知道我们在拍电影。
但因为我们人很少,机器也很简单,比较不动声色,顶多路人会干扰一下来看镜头,但因为我们又都拍很长,回去可以剪。
深焦:最后一个问题,为什么叫《日子》?
蔡明亮:剪完了之后就想片名了,很快就想到“日子”,也没有怎么费力(深焦:就像每天大家里要“过日子”)。
对,因为自己做的事情就是这样,也不需要有多新颖,恰当的就好了。
2020年2月25日于柏林原刊于深焦DeepFocus_2020年2月28日
6 ) 原來喵喵不止一個
喵喵看來是不露臉了 像鴕鳥那樣把頭埋在沙裡 然後 有一群人圍向我 叫我別找喵喵麻煩了 他不過就是普通人 跟我們這的所有人都一樣 如果有犯錯 也不過是普通的錯 不痛不癢的 更有人說 我們都是喵喵 你抓吧 好像在演電影一樣 人們保護了好人喵喵 逃過了壞人蔡明亮的魔爪如果今天又有一個叫汪汪的 在豆瓣或百度 對我幹了同喵喵一樣的事 也就是公開輸送我尚未發行的電影樣帶 不巧也讓我逮個正著 我要求汪汪露個臉 起碼跟我道個歉什麽的 又一群人圍著我 別找汪汪 他也都跟我們一樣 不過就是普通人 不然 我們都是汪汪有人警告我 別點名喵喵 如果有汪汪的話 也別點 傳一條私訊 要求對方刪除連結就算了 否則你會得罪很多人 你的影迷也都會跑掉 我說不 任何一條非法的連結 又衍生出多少連結 永遠都清不完了 一部還沒發行的電影 有著樣片的印記 就這樣在網路上被賤踏了 我不止要找出元兇 也要找出輸送者 他們一個個也都是幫兇 起碼要讓他們知道 他們造成別人多大的損失 犯了罪 就該負法律的責任不解的是 我追兇擒賊 為何會得罪一群人呢 總算讓我搞懂了 原來 喵喵不止是一個人 而是很多很多 都叫喵喵睡前 同事傳了黑梦骑士在豆瓣的留言給我 我難得認真仔細看了兩遍 讀到了哀傷與誠懇 我想回應這位朋友《日子》此刻所受的遭遇真的令我傷心 打擊很大 幾乎令我失望透了 很不想再拍了 如果你真喜歡我的作品 你對我還有尊重 勿看盜版請耐心等待 有那麽一天 在某個戲院看《日子》那才是真的看了 記住 是我的影迷 就別讓人瞧不起 謝謝你要我原諒你 我原諒了 蔡明亮 2020.4.14
7 ) Cinefest之旅:黑色暴雨天看「日子」才是不枉此生
之前因爲第三波疫情取消的HKIFF影展令全港影迷扼腕,而處於疫情互相隔絕的今日世界,搭飛機坐火車去到周邊城市觀看影展也變得不切實際。
但萬幸的是,本港院線重開後,HKIFF立刻以最快速度重新召開了一連五星期的Cinefest影展,精選參展影片以饗影迷。
此前備受期待的大師之作,以及獲得火鳥獎的新人佳片如今重新著裝,在接下來的時間重返大螢幕。
疫情暫緩蔓延,電影魔力再現,觀眾亦久別重逢的領略今年珍貴的影像創作。
Cinefest影展將在K11 Art House大熒幕接連上映 網絡圖片9月30日,本港黑色暴雨天,放映如常舉行,現場依舊人頭湧湧。
電影亦從李康生觀看窗外的雨聲開始,長達十分鐘的鏡頭讓觀眾感受著他的狀態,也與戲院外的暴雨冥冥中產生互文。
與《愛情萬歲》中用空間裝載寂寞的表達不同,蔡明亮近幾年摸索到了新的語法去表達自己。
他的鏡頭語言在一些觀眾看來是過於緩慢的,甚至被看過後一頭霧水的影評人譏諷為「監控錄影」式的鏡頭。
但在此之外,熱愛蔡導的影迷卻樂此不疲的追尋著他每一部作品,並且在觀看如此漫長的固定長鏡頭中尋找到不同於主流電影的快感。
電影第一幕 網絡圖片蔡明亮的長鏡頭其實有很多可以細味的地方,一方面,和《愛情萬歲》中一脈相承的是對於人在孤獨狀態下的描述,影片依舊是寡言的,在更多場景中我們只是看著亞儂燒火,做飯,小康在山林裏聼風聲、針灸院中接受治療,透過幾乎相當於真實流動的時間,我們也在感受著角色當下流動的情緒,演員的表演讓我們能與角色共享一個「知覺場」,亦是產生所謂的「共情」。
另一方面,導演在聲音處的編排演繹了敘事的豐富性,漸強漸弱的雨聲,山林中狂風亂作,或是按摩中不斷變化的幾種呻吟聲,都令本來單調的畫面充滿了可想像的空間,亦襯托出了片中人物綿密細膩的情感體驗。
或許前半段有些鏡頭會使得觀衆覺得枯燥乏味,但這也是蔡明亮想提醒我們的,這就是生活的底色。
而《日子》中所透露出的詩意也不是令人沉醉的,而是帶有禪意的。
片名直白的告訴觀眾影片的主題是關於人如何過活的,這種生活在前半段是關於如何和自己相處的,後半段則是處在人世中個體與個體是如何互相慰藉的。
當李康生惶惶的穿過香港街頭的人群,來到酒店預約色情按摩交易,無論是亞儂來到之前他鄭重其事的備好現鈔,還是激情發洩過後,兩人在浴室輕柔的摩挲身體,這些由身體觸碰而帶來的情欲變奏都令人感到心動。
或許兩人之間已發生過數次的交易,肉體的觸碰停留在表面,意識的交合卻在荷爾蒙燃燒的尾奏下悄然發生。
情感的沸點不是發生在生理上的高潮,而是交易過後,李康生輕輕地送了亞儂一個音樂盒,當其中傳出卓別林的電影音樂,世俗的交易霎時被定格為「永恆」的瞬間。
本是粗淺的肉體慰藉,不經意間,變成了孤獨靈魂相碰的動人時刻。
固定長鏡頭再度顯示出溫柔而堅定的力量,此刻最不明就裏的觀眾也應該明白,這個最容易被誤解的電影技巧,在某些時刻,可以將觀影快感延長數倍,令觀衆享受在普通電影處無法獲得的深度共鳴。
兩人的靈魂交合 網絡圖片蔡明亮在如今的華語影像創作者中顯得睿智而高明,《日子》本身不提供諸多可供影評人和學者分析的符號,也不去玩弄複雜的影像技巧。
影像裡的悲歡離合不是奇觀,卻能讓看後的人黯然神傷。
鏡頭既是在對抗快速的現代化,也如一把準確的手術刀,切割出生活內核裏的清苦、平靜、反復。
他為如何不依靠電影工業拍出一部動人的作品作了一個完美的示範,也爲敘事找到了可靠的落脚點。
縱然有時顯得抽象,但卻言之有物,不會强行擔起大而無當的功能。
這首悠長的詠嘆調由導演本人的生命經驗生發出來,而李康生也很好的在螢幕上承載起了這巨大的能量。
不過最令人感動之處還是他在鏡頭外的慈悲,就像他看到小康被燙到時忍不住出聲提醒,又或是放過了當初洩露片源的犯事者。
這些行為折射出一顆晶瑩的心靈,如電影裏念念不忘的卓別林電影音樂,令人在蒼涼人世間感到一絲溫柔的慰藉。
8 ) 孤独的节奏,寂寞的轰鸣
蔡明亮最爱讲孤独,这次从青春一路狂奔到了衰老,少了些少年不识愁滋味的莽撞,多了些欲说还休的无奈与惆怅。
节奏很慢,慢到我数出来这两个多小时的电影只有大概47个镜头,平均一个镜头将近三分钟。
这给了我大量的时间去观察和思考,和小康一起听窗外雨淅淅沥沥,也和阿农一起生火洗菜做鱼汤。
最喜欢的部分是小康去做针灸,被火烫到的瞬间全影院的人都不厚道地笑了。
Q&A时才知道,李康生是真的病了,蔡明亮拿着dv带他去看病,于是《日子》也算半部纪录片。
而阿农是蔡明亮在泰国街头遇到的老挝打工仔,两人相聊甚欢。
后来在视频通话中阿农在做饭,蔡明亮觉得很有意思,就在电影中设计了这样的情节。
感谢蔡导,我好喜欢看亚洲人洗菜煮鱼吃饭,尤其喜欢看阿农削青木瓜娴熟的样子,这就是在过日子。
于是《日子》的非虚构成分在这时大过虚构了。
这部电影也由此变得完整:两个孤独的城市人,一个被身体与疾病所困,一个被陌生的城市和环境所困,语言不通之时,寂寞让他们的心灵相近相通。
“老挝并不是一个富裕的国家,所以很多人去泰国就业。
一些并不喜欢男生,逼不得已从事这种擦边按摩行业,使得业内良莠不齐,有客人甚至会被殴打和抢劫。
” 李康生讲到这,我才懂得为什么他在阿农来前会把钱锁到保险箱里。
看着小康慢慢走路,慢慢藏钱,慢慢洗澡,慢慢和阿农一起听音乐盒,慢慢睡去又慢慢来醒来,他的节奏总是那么慢,直接影响到了蔡明亮每一部电影的节奏,慢慢就变成了《日子》的一个镜头三分钟。
观众问小康需要为这个角色做怎样的准备,他说自己基本每晚都是一个人度过,这种孤独感根本不用准备。
感慨之余,想到对于小康这样的演员来说,个人现实与出演作品高度重合之时,也许才真的做到了戏如人生。
片中的小康走过了很多地方,曼谷、香港和台湾乡村,但室内都没有什么很高的辨识度。
这也许是在诉说现代人和空间的关系。
相似的场景换了又换,在出行成本如此低廉的今天,地理环境早已不再重要,因为没人避免得了那熟悉的孤独感的侵扰。
从某种程度上来讲,小康的脸就是蔡明亮的电影,不同年纪的小康是蔡导电影的不同面相。
蔡明亮有说过想要拍摄小康60岁的样子,这么说来下一部长片可能是五年后?
伦敦 Garden Cinema 10/09/24
9 ) 《日子》:来不及完成的生活
有些演员和固定导演、特定电影风格捆绑已久,如果出现在其他作品里会觉得违和,甚至不太能接受。
李康生在《馗降:粽邪2》的法师、《楼下的房客》里的同性恋租客,其实很容易让人出戏,像是让一个枪法精准的狙击手打掉天上的云朵,古怪的大材小用。
李康生只有在蔡明亮的电影里才是李康生。
从《爱情万岁》(1994),《天边一朵云》(2005),《郊游》(2013)到这部暌违已久的《日子》(2020),蔡明亮最喜欢拍的是“孤独和寂寞”。
王家卫也喜欢拍“孤独和寂寞”,两个人的寂寞是截然不同的。
蔡明亮是静态的,王家卫是动态的,蔡明亮是灰暗的,王家卫是缤纷的,蔡明亮是痛苦的,王家卫是轻松的,蔡明亮是失望的,王家卫是满怀期待的,蔡明亮不苟言笑,王家卫絮语闲言,蔡明亮的孤独因为压抑的情欲而肿胀而蓬勃而疲乏,王家卫用繁华的霓虹和思绪使孤独对象化审美化,成为自珍自恋甚至享悦其中的艺术。
《日子》是蔡明亮“寂寞”的主题再一次探索,是深化,也是简化,放弃叙事,传达情绪。
《日子》片长127分钟,只有两位主要演员,影片结构是完整的一天,从早到晚再到清晨。
开场就是李康生看着窗外的风雨,满脸疲态,持续了5分钟。
接着是李康生和亚侬各自的生活,洗澡,洗菜,烧火,做饭,逛街,购物,全程基本一言不发。
中间甚至有一段真实的李康生治疗肩背病痛的片段,还因为电击疗法发生意外烧到头发,正在拍摄的导演急切地介入帮忙清理,这段已经是实实在在的纪录片,跳出了虚构和故事。
之后是长达20分钟的酒店按摩戏,观众在大银幕前面对李康生的身体,欣赏完一整套泰式按摩,极为考验耐性。
按摩结束,李康生送了亚侬一个八音盒,亚侬打开音乐盒,流泻出卓别林《舞台春秋》(1952)的主题曲《永恒》。
两个人静静地听着音乐,然后告别。
李康生沉默片刻,又追上了上去。
镜头在远处注视着两人在小店吃饭,聊天。
李康生回去,继续劳作,散步,睡觉。
亚侬回家,烧饭,睡觉李康生第二天早晨醒来,睁开眼,迷茫的眼神,若有所思。
亚侬来到公交车站,仿佛在等什么,缓缓拿出八音盒,听着八音盒的音乐,看着繁华的车水马龙。
他们聊了什么,他在想什么,另一个他在想什么,没人知道。
蔡明亮现在喜欢随机地经常性地保留一些影像素材,没有任何目的,只是单纯地记录。
这部电影的素材是从2014年开始拍,拍到2019年,背景人物的淡化和模糊,让素材也失去辨识的可能,四年多的影像片段结合到一起,观众很难区分出他们是在台北、香港还是曼谷。
在曼谷,蔡明亮决定制作这部电影,拍摄了中后段的按摩戏和片尾的公交车站戏份。
之前零碎的片段在这里突然有了联系。
两个人有了交集就有了事件,两个人分开就有了故事。
八音盒让画面出现了情绪的碎片,一旦有了情绪就有了意义,就可以感受,就可以解读。
蔡明亮依然是对人间有眷恋,即使彻骨的孤独,也不愿放弃。
除了高度纪录片风格的内容、大量固定长镜头,蔡明亮在这部电影里最突出的形式突破是接近于零的电影台词。
除了治病一段李康生和医师有些简短交流,两位主演之间基本都是靠眼神和表情“对话”。
蔡明亮电影台词的简化是近年作品的趋势,在这部电影的开头干脆打出了“本片无对白字幕”。
导演认为“语言是危险的。
”在表达情感的时候,语言不仅是危险的,有时候也是多余的。
李康生坐在窗前发呆,两人按摩完之后的对视,两人一起坐在床边听八音盒音乐,李康生早晨醒来后空洞的眼神,亚侬在公交车站落寞的身影,这些时刻无法用语言表达,那些微妙的流动的变幻莫测的难以捉摸的感受多到复杂到简单到语言无法承载。
不说话的时候表达的比说话时更多。
就像那场漫长的按摩戏,肉香弥漫,情欲淤积,虽然一言不发,但是欲望蓬勃。
它承载了两个人的寂寞,又延续了甚至放大了寂寞。
是开始也是结束。
是可能性。
《深焦》记者采访时问导演,是否“性”在这里很重要。
蔡明亮说:当然很重要。
人与人相处,最后留下一些什么东西,是什么?
这不是一个故事片,我们不用说得很明白。
正因为它不是故事片,它说的不是很明白,所以它很真实,思念很真实,寂寞也很真实,不一定要完成。
生活普遍就是这样,没有事情被完成,完成都是编剧在完成,或者电影在完成。
我不觉得需要完成,所以我现在最感兴趣就是拍没头没脑的电影。
我们长期都被电影的完整性……所“洗脑”,洗到我们习惯、束缚了,看不到更多东西,看到的可能都是假的东西。
我觉得通常真实的都是没有完成的,来不及完成的,或者不会完成的,所以人生才会有感触。
两个男人的一次约会在这部电影里具有了某种象征意义,吃喝拉撒,生老病死,买与卖,爱与被爱,寂寞与等待,这就是生活,这就是“日子”,《日子》就是在讲人如何活下来。
电影的主演之一亚侬,是蔡明亮在曼谷街头偶然认识的打工仔,老挝人,当时是厨师,导演吃了他煮的面,他刚好休息一下,就跟他聊了起来,留了联系方式,有了一些交往。
想拍这部片子的时候,就拉着他一起了。
蔡明亮曾对《明报》记者说起电影的创作:“我的电影和我的生活有很多重叠,哪怕是一个道具,我不会坐在家里写剧本想一个桥段出来,它一定是有原因跑出来的。
《日子》里的音乐盒,是云霖2019年初送我,我们当时去阿姆斯特丹,他帮我在电影博物馆买了一个音乐盒。
后来我去泰国,就送给亚侬。
《日子》里原本没有想到用音乐盒的。
我去了泰国,小康也要来了,然后我就一直在焦虑他和亚侬要不要相遇,相遇是一部电影,不相遇也是一部电影。
后来我决定要相遇,相遇一定有这个情欲戏,那么有什么东西可以超越这种金钱交易的按摩?
我忽然想到音乐盒,就请亚侬把音乐盒拿过来,变成一个道具。
”《日子》就是蔡明亮和李康生的一段日子。
电影在蔡导这里仿佛回归到了最原始的境地,用自己的眼睛,记录生活,感受生活。
影像不再高高在上,它和生活同时进行,不知何时起,不知何时止,永远流淌。
10 ) 《日子》:一天天的度过,波澜不惊,却处处风景。
很多画面几乎都是静止的,比如开场李康生望着窗外,在浴缸的水中闭目养神,云雾缭绕的山上。
标志性的蔡明亮的长镜头风格。
很多空镜就像在看监控,回归生活的原本面貌。
不知道导演到底要给我们看什么,但貌似什么也都包含在镜头语言里。
路边捡来的泰国小哥哥,洗菜做饭,裸露着上身及双腿,新鲜却普通的肉体,一如年轻时的李康生。
从年轻的李康生到中年,甚至步入老年,期间包括他的中风,蔡明亮所有的电影几乎都与李康生有关。
在感叹“长情”、“专一”的同时,作为观众,我们也见证了一个男人传奇却也平凡的一生。
从最开始《青少年哪吒》、《爱情万岁》里的青涩与质朴,但《河流》、《洞》里的怪异与探索,再到《不见》、《不散》、《天边一朵云》、《你那边几点》时期的成熟与绽放,以及后来《行者》、《无无眠》、《无色》、《郊游》、《日子》中的落寞与衰退,我们看到了每一个时期李康生的变化,以及作为观察者、记录者蔡明亮的变化。
电影进行到一半的时候,此前各自生活的李康生和泰国小哥才有了交集。
酒店房间里,暧昧性感的情色按摩,两人从始至终没有言语交流。
泰国小哥业务很纯熟,估计以前在泰国也是马杀鸡的高手,全程服务非常到位,看得出来,李康生也很享受。
激情之后,是音乐盒里美好童真的音乐,两人坐在一起,就那么安静的听着,画面,还有我们的心,又静止了。
最绝的是临近结尾的一组镜头,李康生从睡梦中醒来,睁着眼睛,长时间的定格特写,视觉上,没有任何的变化,但那呆滞与空洞,难道不是我们日常最熟悉的眼神?
日子,一天天的度过,波澜不惊,却处处风景。
PS:李康生做针灸、刮痧,火烧到头发;还有被马杀鸡全程赤裸身体,任另一个男人摸遍全身,当演员真不容易,身体不是身体,而是工具。
李康生从某几个角度观察,越看越像王志文。
作者:蓝雨星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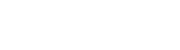










































这是在干什么.jpg
6/10。烧煤,切菜,煮饭,洗澡,时而坐着,时而躺着,空白而毫无特色的现代公寓中承载着寂寞的分秒流逝,简洁的构图依然聚焦于纹丝不动的李康生,开头李康生凝视着窗外的暴雨,一条白色的反射光穿过他头部,犹如时间留在李康生脸上的刻印,暴雨倾泄着劳累和欲望,去针灸的李康生背上满是金属块、电线和发烫的玻璃圆球,缓慢地铺层疾病隐喻的孤独、痛苦状态。泡入浴缸的李康生向上凝视,参天大树、云彩峡谷的过场画面然后是穿着粉红色短裤的亚侬,壮丽的风景衬托出年轻身体的诱惑力,镜头开始漫游在门是木板拼接的简陋居所、高速公路的候车站、沿着车顶一排滑落的雨滴、夜市旅馆等各自生活的空间,两颗异地的心透过倒油按摩的肌肤之亲,寻找着彼此空虚落魄的抚慰,顺着腿按摩到臀部和胸肌的身体接触脱离了滥情色彩,通过音乐盒礼物牵连起真诚的情感交流。
意外,一部电影令我确认了自己那段爱情的有效性。就像通过每天照镜子这一动作来完成对自己的确认;蔡明亮太会拍情欲了,我猜他一定也是那种会在爱人离开后的房间里贪婪猎食对方气味的动物,不然推油那场戏结束两人都离开后唯独摄影机还久久待在原地。至此,我的身体也已经完全打开。
【蔡导别骂我看完片源立刻删除了】无字幕对白就是在删符号,删繁就简,但是简单本身,对我来说毫无吸引力,一如“日子”,流水的日子,普通至极的日子,死水的日子。电影不造梦了吗?人活在梦里还是日子里呢?三星半。ps李康生的肉体怎么这么美好?
#LFF2020#
[2022.07.17 @GZPJ·太平洋的风3] + 贴片《良夜》⭐️⭐️⭐️⭐️
《河流》到这一部,贯穿的是肉体之痛与情欲的关系。有几个镜头宛如神启。但不如把意义再稀释一点,“八音盒”这种(过时)意象就不必了吧
能耐著性子看完我服!唯一的亮點是李康生有三個奶頭??之前怎麼沒注意過!是看錯嗎?
蔡明亮现在的作品更能体现出大银幕的重要性来,在无限拉长的影像时长内,并无更多直接吸引注意力的情况下,大银幕成为最好观看空间,随观影方式由观看荧屏的越小变的越便捷,观影者投注的注意力也是随着下降的,只有巨大银幕以一堵墙似的存在于目光所到之处,给出进入缓慢电影的最佳入口下,我们才能认识到电影最完美的播放媒介空间——影院。相较于组接到一天之内的发展脉络,拍摄四年的对比凸显出这部看似生活流电影下的精巧,或者说蔡明亮处理素材超乎寻常的能力,无目的素材积累在交织中流向设置出的两人相遇,并碰撞出日常的情感瞬间。拍摄背景的不统一性也被改写为同时代下的城市荒芜人心,随意音乐的加入也能触发内心情感的波动,这看似随意的设置也点明了蔡明亮现在的创作逻辑,在无目的的日常积累与创作中自然呈现的主题内涵,或称灵感的显现。
今生仿佛是为了那叮叮咚咚而来
太太太好睡了,推荐给失眠的朋友,蔡导真的没有拍着拍着就睡着了吗…还是蔡明亮一如既往的“反电影”,视听语言被精简到极限(这次连对白都省略了),但相比行者系列那种孤身对抗消费社会的英雄主义,本片就更像是一首苍白的散文诗了。作为一部基片,在豆瓣只收获六分,说明了一切。
镜头是真的越来越长了。我还是最喜欢《爱情万岁》《天边一朵云》《郊游》。
男人的浪漫总是在来一发之后,这也是男人抵抗虚无的终极意义。
Moma film screening 1. 李康生今天生日,蔡明亮今天拍电影30周年。“日子”对于阿康来说即是我是一颗石头,我只是被放置,我几乎不交互。在街头我总是猜是哪个城市,想象里连结到无数个茫然的瞬间。这几天看到一个有趣的故事,睡一觉醒来好像是前世,小马想我到底是老陈还是小马,后来老陈想我的上辈子一定是小马。看这个电视的感觉就是我好像是一个mixture,一些相似的记忆,还有极少出现的一种下午外公坐在阳台看鸟,外婆坐在门口看娃的空荡荡的感觉。音效替代了阿康和Non的交流,音乐盒是唯一诉说的温柔的关于爱的语言,其他都是漫长的没有回音的solitude。又:怎么会在一起吃面条啊,泰感人了。
真的是日子,也真的是不想看的日子。
蔡明亮的片子到近几年的这几部 都是静心助眠利器 主观性的纪实画面 观众过着小康的每一分钟 也是蔡明亮的每一分钟
非常矛盾 这是四两拨千斤的震撼 是无法复制的观影体验 但以后我也绝无耐心自己在家看蔡明亮
李康生又一次脖子出问题,上一次出问题时他和爸爸来了一发,可没治好脖子。这一次大保健治好了脖子,可见蔡明亮是反对乱伦的…....
开篇康住在山上,包裹着他的是风雨声和阴暗相间的光影,NON住在城市里,包裹着他的是嘈杂的汽车声音和铁栅栏,康得了歪脖子病,他不得不走出这个避世空间去香港治病,NON每天的生活似乎早出晚归,平淡又神秘,摄影机开始移动起来,人流出现,社会公共空间开始取代私人空间,康来到泰国,找了个按摩的,两个人突然在一个镜头中相遇了,他们直接开始肌肤的亲密接触,渐渐地康的眼睛开始注视NON,私人空间中开始出现了两个人,康送NON八音盒,电影中出现了音乐,一起吃饭,公共空间中出现了两个人,孤独被情感击退了吗?结尾康的自然环境中出现了嘈杂的人声和机械声,而NON在城市中听着八音盒,原来他们都没有治愈孤独的病,而是背负了两个人的孤独,蔡明亮用极简的视听创造了复杂的、充满隐喻的空间形态,在此之下,日常也充满了象征,留白也在叙事
你在疯狂示爱,而我倍受折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