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邪恶不存在》剧情介绍
一对住在东京近郊山村的父女,过着恬静简单、顺应自然的平凡日子,直到村里盛传有开发商要将森林打造成豪华露营区,希望能让居住在市区的男男女女有个可以逃离无聊日常的后花园。而这个为大家好的计划看似能为村人带来经济效益,却会破坏山林的生态环境,更将打乱居民的生活...热播电视剧最新电影隔墙有眼公正裁决怒火追凶末日病毒恶种麻烦三角错白宫风云第三季太平间闹鬼事件狄仁杰之大幻术师小本经营金与银电台之星99.9:刑事专业律师-完全新作SP全新的相遇篇~大欺诈师爱的暂停键无人机代号RZ-9单身宿舍连环炮真心遇上大冒险Link:尽情吃,用力爱邪恶不存在狎鸥亭白夜情定爱琴海战·无双异星灾变第一季惜花芷心结千千流金岁月巴斯克久远时光卧底使命·火线追凶窃贼、妻子及皮划艇乱世丽人行
《邪恶不存在》长篇影评
1 ) 邪恶不存在?邪恶不存在!
作为当今世界影坛最重要日本导演之一,滨口龙介本可以借着《驾驶我的车》的顺风车,继续一路畅通。
但是他偏偏选择拍摄一部本不在计划之中作品。
这部原本为音乐家石桥英子所做的影象MV,最终被扩充成为一个半小时的电影,就是2023年威尼斯金狮奖提名作品《邪恶不存在》
电影用极其克制和冷峻的镜头语言,讲述了在一个关于东京近郊山村的故事。
托海父女本来过着平静安静的山中生活。
父亲整日在村子里帮忙打零工,砍柴、接山泉水、巡逻等等。
生活虽然平淡,但是自由自在。
女儿更是天真单纯,她喜欢放学后,穿过茂密的原始森林徒步回家。
神秘的森林在女孩眼里简直是绚烂的天堂,各种动植物如数家珍然而,这平静的生活,被一家计划在这里建造豪华露营的经纪公司打破了。
在他们眼里,追逐经济利益是第一位。
规划图不仅漏洞百出,还会在日后严重影响当地人的生活。
为此,村民和经纪公司展开了激烈的斗争。
为了缓解矛盾,也为了加快工程推进进度,经纪公司代表决定雇佣托海为营地管理员。
然而,当一切都在向着缓和发展时,托海的女儿却横遭意外
电影不但讨论了现代文明与自然的关系,同时也作为一部后疫情时代电影,映射当下日本社会的底层情绪和生活状态然而,这部情节上看似矛盾冲突激烈的电影,在影像表现上,却格外的克制和冷静,开场将近一分钟的仰视镜头,缓缓穿过原始森林。
好似将观众拉近那个远离人类文明的空间,感受自然的呼吸电影更是在极少的对白中缓缓展开。
在这片土地上,人与人的距离是遥远的,与自然的距离却是贴近的。
沉默的行走,沉默的劳作,让整个环境都沉浸在自然的噪音中。
而戛然而止的音乐声与嘈杂的争吵声,全部被导演刻意设置为人类文明入侵的信号直到远处的枪声响起,冥冥之中大自然完成了对人类的报复
电影中的人物关系主要分为三类,原住民(以村长为首的老人,托海父女)、外来定居者(托海父女,拉面店夫妻)、外来入侵者(经纪公司职员)他们之中唯一的变量,就是外来定居者,他们深爱着这片土地,却又无法抵御外来的诱惑。
他们享受田园生活的闲适,却又对现代文明的物质、财富欲罢不能。
于是,在对方的劝说下,托海接受了成为营地管理员的工作。
这份工作看似一箭双雕,即保证了自己留在山中的生活,享受这里的自由,又极大提高了自己的收入,满足现实生活的物质需求但是,在自然面前,哪里又既要又要,残酷的惩罚伴随着一声枪响,降临在托海女儿身上然而,就在枪响之时,托海正带着经纪公司的职员,停在山下路边。
此时对方正惊喜的讨论着枪声的来源。
对于城市里人,枪声是如此的陌生,让他们异常兴奋。
正如第一次尝试劈柴的高桥。
对于山里人来讲,这是多么稀松平常的事情,但对于他来说,就是巨大的挑战在影片结尾,狂野湖面上突然闪现的女儿与小鹿身影。
你无法分辨倒在眼前的是被误杀的女儿,还是被猎杀的小鹿。
但是失控的父亲,却突然暴走,狠狠掐住高桥的脖子,试图致对方于死地这种突如其来的施暴,是父亲因为后悔自己为接受工作,忘记接女儿放学,导致女儿丧命的懊恼?
还是他因为外来世界,被唤醒的恶念?
我们不得而知就像滨口龙介在采访中解释道:“邪恶就是假装知道你不知道的东西”换句话说,邪恶就是欺骗托海欺骗了山村,他明知道,即使自己担任管理员,也无法改变营地对自然的破坏,对山村的影响。
但他还是答应了。
托海也欺骗了女儿,因为他明知道女儿是如此真爱这片土地,但他却成了破坏这里的帮凶。
托海更是欺骗了自己,他口口声声说自己是第三代开拓者,想要保护这里,却最终成为真正的“凶手”电影中对于邪恶的惩罚,同样展现在对经纪公司黛和高桥身上。
身为女孩黛本想从事演艺工作,高桥甚至曾经还是职业演员。
然而大环境的变化,逼迫他们不得不从事不喜欢的工作。
纵使有再多的抱怨和不满,也要为了生计坚持
甚至他们还要为了拿到政府补助金,不顾环境破坏,加快营地建设的推动者。
而这样的恶,也让黛受到了自然的报复,被有毒的荆棘划伤手掌,而高桥则几乎被托海掐死在山林里片名《邪恶不存在》,可以是疑问句,也可以是感叹句。
只是片名的背后都揭露了一个事实,那就是邪恶本无处不在,是否作恶,决定权只有当事人能决定当托海抱着女儿的尸体,跑进远处雾蒙蒙的山林,这是导演对人性最后的怜悯。
他相信,父亲会带着你们回到自然的怀抱,父亲也终于意识到自己内心的恶。
这一次奔跑,是一种救赎,也是一种修行电影最后一个镜头,应然是一个仰拍森林的移动镜头,与开场镜头完美呼应。
只是此时的天空已经半黑。
对于大自然来讲,这里似乎什么都没有发生过
2 ) 完美的和谐:滨口龙介对谈石桥英子
· 编者按 ·滨口龙介导演的《邪恶不存在》于近日上线流媒体,在刚刚结束的北影节中也有展映。
影片在2023年威尼斯国际电影节大放异彩,最终拿到了评委会大奖。
前不久,本片还斩获了亚洲电影大奖最佳影片。
相较于大部分影片,《邪恶不存在》的独特之处在于,这是一部由音乐主导的影片,音乐家石桥英子在这部影片制作过程中的重要程度,与导演滨口龙介相当。
某种程度上看,甚至可以说这是一部由音乐家主导的电影。
而作为导演的滨口龙介,也以非常开放的心态对待这次创作,他来到石桥英子日常创作的空间,因一次偶然的机会找到了叙事。
滨口龙介2021年拍摄《驾驶我的车》时,和作曲家石桥英子有过合作。
当时,石桥让滨口为她拍摄一部影片,用来搭配她的音乐新作《馈赠》的现场表演。
而《邪恶不存在》来自于滨口龙介的一个愿望,他希望继续发展在为《馈赠》拍摄素材时组织起来的原材料,并充分调用《馈赠》中的演员,最终完成了创作。
相较于最先委托的《馈赠》,《邪恶不存在》却是先进行剪辑并完成的项目,当滨口剪完片子之后,石桥配了一段可以在《馈赠》之中使用的音乐。
《馈赠》在今年的香港国际电影节也有展映,并由石桥英子现场奏乐。
今天,我们通过一篇来自《视与听》对滨口和石桥的采访,一起走进这部电影奇妙的创作过程。
完美的和谐滨口龙介对谈石桥英子译者:冬寂網路 (高速运转的机械进入中国。
)日本导演滨口龙介曾在2021年拍摄影片《驾驶我的车》时,和作曲家石桥英子有过合作。
当时,石桥让滨口为她拍摄一部影片,用来搭配她的音乐新作《馈赠》(Gift)的现场表演。
石桥对电影并不陌生:她曾经为自己制作的短片配乐;2020年,她还为赖纳·维尔纳·法斯宾德的《世界旦夕之间》(1973)创作了新配乐;2022年,她的爵士/合成器/流行专辑《For McCoy》灵感来自萨姆·沃特森(Sam Waterson)在《法律与秩序》(1990-2010)中饰演的角色。
《馈赠》去年在比利时根特电影节举行了首映,根特也是世界电影原声学会奖(World Soundtrack Awards)的颁奖地点。
电影节受到石桥和滨口不同寻常的反向创作过程的启发,委托其多年来合作的电影人和作曲家制作了25部短片:在这25部短片之中,音乐的重要性要大于影像。
《馈赠》海报然而,《馈赠》也催生了另一部作品:滨口龙介的新长片《邪恶不存在》,该片获得了2023年威尼斯国际电影节评审团大奖。
它来自于滨口龙介的一个愿望,他希望继续发展在为《馈赠》拍摄素材时组织起来的原材料,并充分调用《馈赠》中的演员,这些演员在《馈赠》之中没有一句台词。
《邪恶不存在》不出意料地将配乐(当然也是由石桥英子负责)放在首位,并将其发生背景的森林的声音作为核心。
影片以一段推轨镜头作为开场,摄影机角度朝向天空,前方的树林若隐若现,几分钟后,石桥的配乐随着弦乐的膨胀和渐弱,从一种情绪转换到另外一种情绪,从和谐到不和谐,从平静到焦虑,为这部阴森怪异的影片定下了基调。
《邪恶不存在》是一幅缓慢而催眠的画像,描绘了东京附近的一座山村里,单亲父亲巧(大美贺均 饰)和他年少的小女儿花(西川玲 饰)在这里打零工,过着和平安宁的生活。
巧是个沉默寡言的人,乐于花大量时间沉浸在大自然中——他和来自东京的闯入者高桥(小坂龙士 饰)、黛(涩谷采郁 饰)、以及傲慢的会社长(宮田佳典 饰)有着明确的冲突,因为社长让高桥和黛说服当地人在该地设立据点,而他们的开发计划很可能将会影响到该地的动植物。
但《邪恶不存在》绝非说教的生态预言,正如其谜一般的标题所示,它是一部真正的视听诗歌。
我在根特和滨口龙介、石桥英子聊了聊。
《邪恶不存在》剧照Elena Lazic:你为什么选择现场配乐这种形式?
石桥英子:我对音乐和画面的对应关系以及它们如何相互配合很感兴趣。
我非常喜欢电影,我一直很好奇什么样的形式可以让电影和音乐共同存在,彼此关联。
我每次的现场演奏都和之前有些不同。
我很想知道,随着现场演奏的不同,人们对于观看影像的感觉能有何种不同——反之亦然,每一次观看影像都会影响我演奏音乐。
每一次,这两种影响都彼此不同,这正是我想要体验的东西。
我脑中的东西并不是那种伴随着抽象画面的演奏。
我希望伴随着音乐的更像是一种类似故事的东西。
我让他(滨口龙介)配着音乐写一个精彩的故事,写点令人兴奋的东西,因为我已经感觉到了他的影片有一种音乐感——即便是对话场景。
我相信,如果你不看画面只听对话的话,那么听起来就像是音乐。
《邪恶不存在》剧照滨口龙介:我接受了石桥的请求,因为我认为这会很有趣,但我几乎将近一年的时间不知道自己想做什么。
我一开始在想如何让音乐和故事彼此适应,后来我参观了她做音乐的地方,想知道是什么样的环境。
我到了那里以后发现它位于一片自然环境中间,这就是为什么我会想到我的作品需要大量的自然景观的画面,她的音乐配上自然元素很合适。
我看到她谱曲的地方也是她的家,所有的窗户都是开着的。
当然,如果你在城市里面这样的话就会让人感到很沮丧。
但在这里,声音能从里面传出来。
同理,外面的声音也可以传进来,例如鸟儿和其他自然的声音。
此情此景对我而言算是一个转折点。
它让我看到了我该如何处理影像。
《邪恶不存在》剧照当我开始为影片寻找一个叙事的时候,这里突然开始出现了一个露营的项目。
从这个意义上说,这几乎是象征性的,因为我感兴趣的不仅是自然,还包括自然中的人。
人们突然开始介入自然,特别是一群来自城市的人介入。
我感兴趣的是,一旦人们进入这里,将如何影响自然环境,以及二者如何开始互动。
从这些事件之中,电影几乎自然而然地启动了。
英子的一个朋友向我介绍了一个本地社群,我们足够幸运地和当地人搞好了关系。
就像在影片中所提到的,那个地方历史上长期无人居住,在二战之后人们才开始住在这里,这里是乡下,但似乎他们并不是世世代代都住在这里的。
《邪恶不存在》剧照Elena Lazic:演员是否听了英子的音乐?
你是怎么执导演员的?
滨口龙介:有的提前听过。
有一次,我们和她和乐队进行了一次测试,(长期和石桥英子合作的)吉姆·欧洛克(Jim O’Rourke)也参与了,我们录下了音乐,随后弄了一些测试镜头。
当我们做测试镜头的时候,全体演员都在场。
事实上,主演只不过是演职人员的一部分,而成员之中很多人根本不知道她的音乐,更没有提前听过。
我一开始只是为了《馈赠》拍素材,但是随着《馈赠》的素材出现之后,演员的表演为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我认为如果我不把素材都用上,那么我就会对他们于心有愧。
有人建议我可以用这些再做一部电影,我问英子能不能拿这些素材再单独做一部电影,她回答可以。
最后《邪恶不存在》是先进行剪辑并完成的项目,当我们剪完片子之后,她配了一段可以在《馈赠》之中使用的音乐。
所以《馈赠》才是这次合作的最终成果。
《邪恶不存在》剧照Elena Lazic:你提到了石桥英子在大自然之中的房子里面谱曲。
在《驾驶我的车》之中的话剧导演也做过类似的事情,他在创作的时候让自己隔绝于外物。
你们两人在《驾驶我的车》之中也有合作,配乐也在这部电影之中扮演重要角色,这段合作和《邪恶不存在》有什么不同吗?
石桥英子:当然,最大的区别是,在合作《驾驶我的车》之前我们并不认识。
所以一切是从“请多关照”开始的。
我们一开始都有点小犹豫,因为不知道自己究竟应该做些什么。
但是后来,我开始收到画面,一切就变得迎刃而解。
从这种意义上讲,我们这一次的合作也没有区别,因为也是一个来回的过程,我收到画面,给他音乐,直到最后完成。
滨口龙介:当然,我们不能一直形影不离地合作。
最重要的是画面和音乐目标一致,二者不能割裂开来,必须是合二为一的。
但是另一方面,我们也应该有各自离开对方,单独创作的时间,然后再回来,流程一遍遍地继续。
我们已经在《驾驶我的车》里这样做过,当然,为了这次的项目,我们可以花更多时间,真的是太奢侈了。
石桥英子:当我看到《馈赠》的成片时,我也开始使用新的目光来看待周围的事物。
我一般用钢琴和合成器作曲......我一开始根本想象不到会用弦乐,但我看到了送过来的成片之后——当然,不仅仅是风景的影响——我也开始考虑通过不同的方式谱曲,并开始制作弦乐的谱子。
或许是因为我认为弦乐最能表达大自然的灵性,以及滨口龙介沉默的愤怒。
特别有趣的是弦乐在其他场景中使用了好几次,比如说黛拿着一个大水箱的时候,我认为这是对音乐的一种独特使用。
《驾驶我的车》剧照Elena Lazic:《邪恶不存在》有着很有趣的调性,有的时候特别伤感,有的时候特别恐怖,有的时候又特别搞笑。
听着石桥的配乐——特别是和麦考伊合作的几段——我有着相同的感觉,你的音乐经历了许多不同的情感:有时它是相当严肃和忧郁的,但也有一些相当有趣和几乎是荒谬的时刻。
您在合作时讨论过这个语气的问题吗?
还是仅仅是因为彼此有同样的兴趣?
石桥英子:我们并没有刻意讨论过这个问题,但是我看过他为2011年东日本大地震以及福岛拍摄的纪录片。
尽管是很沉重的主题,但仍然存在幽默的片段。
我认为我自己做不出来。
但我很佩服那些在表现重大或者严肃主题的时候还能见缝插针地插入很多引人发笑的东西的人,我真的很敬佩他。
滨口龙介:我不是有意这样做的,我很少会下意识思考:“我想在这里让观众笑。
”更像是我在写些什么的时候,最后我自己也笑了。
《邪恶不存在》剧照Elena Lazic:《邪恶不存在》和你其他的影片有所不同,特别是《驾驶我的车》,因为里面有太多的悬疑,不同之处更体现在结尾:没有太多的对话,取而代之的是沉默,以及音乐的空间。
你是否认为这种悬疑感来自电影制作的方式?
因为事实上它来自于音乐,而音乐又有着开放的解释空间。
滨口龙介:我认为某种悬疑对于电影而言是必不可少的,因为在我们生活的世界里,某些时刻,人们也遭遇着各种各样的谜。
在我的电影里,一些事情会半路开始,或半路结束,这是很常见的模式,因为这就是我们对生活的体验,有的事情会开始,有的事情会结束。
我同样在想,对于观众而言,你需要创造一些东西,让他们与它们不期而遇,并以一种让他们能够理解的方式来展示。
但是这一次,伴随着石桥小姐的音乐的影响,当我思考如何让观众更容易理解某些事情时,我想我可以拥有音乐的神秘品质,这给了我额外的勇气去走某些道路。
《邪恶不存在》剧照- FIN -
3 ) “这简直是天衣无缝的计划”
一早看到字幕组出中字了,马上下载。
(一开始因为声画不同步分心了一会,后面就很能进入了)因为正好最近在读《那些欢乐时光》,对滨口的创作和审美追求有了更多了解,尤其是声音理论。
那段gamping 宣传片的旁白真是离“美好的声音”最远的了。
说明会上,男职员唯独一次没有拿起话筒,下意识地回答了村民的质问,那声はい是带着真诚的。
劈柴后声称是“人生二十年来最畅快的瞬间”真是可疑。
应该说,滨口是以这种方式,不带感情的真诚的声音,和糟糕的表演性的声音,区分角色的世界观。
女职员上一份工作是护理,和 Satoko 相视而笑,《欢乐时光》对于演员们是很珍贵的经历吧。
关于Hana的死,到结束也没太明白,不知道是蒙太奇还是写实,漫天的大雾确实是在男职员倒地才消退,但想想应该是后者,父亲看见在危险边缘的女儿选择不发声不行动,也许是顺应鹿的习性,给生长于这片土地的精灵——hana真正理解和回归自然的自由。
邪恶在自然中不存在,是在利用自然的无知人类中存在。
一开始父亲接hana晚了,开车把正在玩躲猫猫的孩子驱散,呈现了有机和无机的两条逻辑,与后文呼应。
关于镜头语言,村民们看到野山葵和半矢时采用了正反两种镜头,自然也在看着人类。
前半段自然描写以水流和森林为主,多是不带反思的日常行为,后半段则出现了更多动物,并且“对峙”感更强。
整部片子除了末尾寻找hana,更多是固定机位,呈现客观叙事;而配合不间断的寻人启事广播,摇晃的镜头、湍急的水流一下抓住观众的心跳。
类似的主题联想到《北国之恋》那场风暴。
提案在现实和视频会议中错开落下,也是对技术的讽刺吧。
关于配乐,确实片头插曲出现时有些诧异,滨口好像很少让音乐如此有主导性。
但依旧很享受他的台词,以及创造出的空间氛围。
不到2小时,一开始觉得时长不够看不过瘾,看完觉得基本把他想表达的说完了,而且看不到说教感——那样就跟滨口自身的哲学背道而驰了,相比之下,《怪物》的态度比情节更令人窒息。
男职员说“那简直是天衣无缝的计划”,就跟他根本没劈过柴,一斧头下去被木头嘲笑,别瞧不起自然了。
4 ) 净化论带来的邪恶
滨口老师采用了我非常喜欢的、曾经在【欢乐时光】中饰演一向温顺但冲动出轨的主妇樱子的业余女演员、菊池叶月,同样在本片中作为乌冬面店夫妇中的男主人、也是【欢乐时光】中的一个丈夫的饰演者。
我很高兴本片回归了【欢乐时光】开创的一种新小津主义风格:人物和故事在时间轴上被人为的调低了倍速,观众可以更加专注地凝视影片人物的动作,本来就不多的对话也同样被放慢,每一次的转场都留给观众足够的时间去思索;如此每一次的留白、却没有让我感到情节上的不连贯、看下来依然顺畅自如。
或者说,滨口老师已经极大的弱化了情感、简化了冲突,很少有大哭大笑,大声说话都很少(仅有的一次还被嫌弃),然后人物几乎面无表情、礼貌的近乎冷漠。
我可以明显感受到一种压抑和压制、导演不允许演员有任何发挥、任何多余的动作都会破坏整部影片营造的气氛。
这种新小津主义的风格,就如同浓墨重彩的画笔、严厉而毫不留情的洗刷掉所谓的“邪恶”,在这种粗糙又暴力的粉饰工作之后、人与人之间的热烈交流、家人的亲密接触、乃至男女之间的暧昧、统统看不到了。
就像影片里描写的山村、成年人的生活机械而且死板,反而来自东京的人还带着一些人情味儿呢,哪怕是世俗的虚伪和狡猾。
由此也就引出影片的主题:追求100%净化程度的不择手段、或者是放任5%排放的同流合污,到底哪一个更邪恶呢。
发展到影片的末尾,作为彻底的净化论的执行者的父亲、宁愿目睹自己女儿去替他人赎罪赴死、而不能容忍来自东京的外人破坏这一幕。
影片最后发生的场景,我们很难揣测男主角的心理活动、他如何拿捏自己的女儿与大自然的位置、然后如何迅速的做了决定。
导演花了前面的大块头的时间作铺垫,男主角的最后的行为似乎也不令我意外,说不定山村里的其他人也会采取同样的方式。
滨口导演讲了一个很妙的故事,片中也特意强调了平衡,那么环境与人类之间的平衡、怎样维护这种平衡,每个利益相关方的出发点不同。
其中的追求极致理想的人,在他们的眼里净水器必须100%开动、做到100%净化,如果未达标,就有可能采用净化论消灭异见者、必要时甚至牺牲自己或家人。
不存在邪恶的世界,比邪恶本身更加可怕。
5 ) 【译】滨口龙介谈《邪恶不存在》
作者 | Clinton Krute2024/5/13《GIFT》是滨口龙介新片的另一个版本,这是部重新经过剪辑的影片,在作曲家石桥英子的演出现场无声播放,她也曾为滨口龙介的重要作品《驾驶我的车》配乐(2021)。
《邪恶不存在》与《GIFT》彼此呼应,二者的情绪和表意有所不同,但立足于同一个故事:一个村庄的居民们反抗东京一家公司在镇上建造露营地的企划。
《邪恶不存在》在去年的电影节上大放异彩,目前正在上映,滨口讲述了这样一个故事:刚刚丧偶的拓海(非职业演员大美贺均饰演)是一名当地的杂物工人,同时也是林业专家,他为一家乌冬面馆打清泉水、采摘野生山葵叶,带他的小女儿了解受伤的鹿有多危险,还有野鸡羽毛的音乐属性。
影片中途出现了一个如外科手术般精妙且非常有趣的市政厅场景,乡民们驳斥了那些城里人的商业计划,故事出乎意料地出现了转折,接着露营公司的两位代表登场。
最后,影片又回到了村子里,留下一个完全不予解释的挑衅。
《GIFT》上周在美国林肯中心电影协会首映,在石桥英子变幻莫测的乐律烘托下,已经看过《邪恶不存在》的观众可以看到电影主题如何以梦境般的逻辑重新诠释。
开篇的场景凸显了声音与图像间的不和谐关系:当镜头沿着丛林地面缓缓移动,透过树冠向上凝望,石桥蜿蜒层叠的和声传达出冥思与厄运。
她流畅的音调韵律与滨口的影像交织,经过剪辑的影像分裂了时间线,将《邪恶不存在》通透的哲学性叙事转变为一种更加不详的预兆形式。
我和滨口龙介探讨了《邪恶不存在》中与石桥英子的密切合作,影片与其斯宾诺莎式片名间的张力关系,以及他想要营造的意味深长的困惑与混乱,等等。
Q:这个片名从何而来?
你是在影片拍完后还是之前就想出来了呢?
A:是在写剧本之前,那时候我开始调查研究,在石桥英子居住的地方待了一段时间。
在那儿我想好要拍摄大自然,我想过如何用一种不同的方式去描绘自然,然后我想到了“邪恶不存在”这句话。
这个故事和片名可能会让人们想到人类社会中的道德存在问题,但结局是破灭与崩塌。
Q:你花了很多时间在自然中度过吗?
你本身是露营或徒步爱好者吗?
A:我本身不是一个经常徒步和露营的人,是因为这部电影,我才和大自然有了如此深刻的接触和交流。
Q:据我所知,这个拍摄项目是源于你和石桥的合作,可以谈谈你们是如何一起完成这个项目的吗?
A:这要说到2021年底,石桥英子问我是否愿意为她的现场演出做视效,那之前我们合作了《驾驶我的车》,我觉得和她一起工作很有趣,所以我答应了。
那时候我还不知道她想要怎样的呈现,所以我们互相发邮件,写信给对方,交流想法,直到我慢慢意识到,我想要拍摄她的音乐创作。
我们去了她的住处,看到了她工作和生活地周围的风景,在一个身处大自然中的房子里,她就在那里做音乐。
她转动按钮,在非常安静的自然风景中发出很响亮的音乐。
看着她我开始意识到我想拍的——她的音乐一定受到工作环境的影响,就是那时候起,我开始做之前提到的那个调查研究。
Q:这个故事是从何而来的呢?
A:我和摄影指导北川喜雄一起外出去看拍摄现场的情况,司机是大美贺均,他饰演影片主人公拓海。
此外,石桥英子还向我们介绍了她在这里的其他朋友,其中有一位自然专家,给我们讲了关于树木的情况,还有水的源流。
他已经七十岁了,同时也是老议员中的楷模。
我们和很多当地人都进行了交流,在此过程中我们听说有一场关于露营的市政会议,几乎和大家在影片中看到的一样。
我将这件事作为故事核心。
我四处走访调查,听取大家的意见。
而听了这些人所说的,他们也成为了人物的原型。
有一点很重要,最终的目的是为石桥英子的演出做视觉创作,所以我需要大量可以自由使用的素材。
这就变成了一个复杂的过程,但我决心拍一部电影,以此作为素材的源头。
我想,通过拍摄《邪恶不存在》,我们会拥有大量可以重新用于《GIFT》的素材。
最初,我们并不打算将《邪恶不存在》作为一部独立的电影发行放映,但自从我们开始拍摄,就相信它是值得的。
Q:之前,你曾谈到说排练和遵循剧本对你的电影创作来讲非常重要。
但这部电影的制作与构思中,似乎即兴发挥更多一些。
是这样吗?
A:这个问题有点难回答,因为这要看拍摄中的哪些可以称之为即兴发挥。
但我想说,剧本的确是在调查研究基础上创作的,大概90%的拍摄都是根据剧本进行的。
当然,也会有些意料之外的,例如,副导演发现了鹿宝宝的骨头,然后我们就拍摄了。
我们还碰巧拍到了野鹿,我想到可以用它来创作一组很梦幻的镜头。
但总体来讲,我们还是根据剧本进行拍摄的。
我不确定这算不算即兴创作,但说到底,在拍电影的时候我在努力捕捉瞬间巧合。
我会和演员们一起工作,读剧本,但这不意味着将他们束缚在剧本中,而是让他们有所准备,这样演员们可以更真挚地表达自己的情感。
在这个过程中,我们也能够邂逅更多巧合,而这也是一种即兴创作。
Q:你说过,拍这部电影的过程中你想要营造一种困惑与混乱。
A:当有人问我该如何理解或面对这个结局时,我想说的是:这正是这部电影想让人们发出的疑问!
可能我的思维方式有些矛盾,但我创作的故事中,每个角色都有他们自己的生活,我也是这样引导他们的。
某种程度上,这意味着我们永远无法完全理解他们。
我想,这样的结局方式就是我对影片反响的一种回应,同时我也想表达,电影是一种无法理解的事物。
Q:每次看这部电影,我都能在这种困惑中产生更多的想法。
A:归根结底,我在创作某种程度上接近现实的故事——我想探寻人们为什么做出这样的举动,并尽可能贴近现实地进行描绘。
但我所使用的摄影机机位同时创造出一种虚构,这两种想法之间存在着矛盾。
但对我来说,拍电影就是一种矛盾,虚构就是一种矛盾。
尽管我们终究不知道人物在影片中做了什么,但世界上我们不知晓的事情还有很多。
我希望我的电影能用这种方式贴近这个世界,成为世界的一部分。
6 ) 随口说说
濱口在新作中把题材的探索指向自然与人不可调和的矛盾关系,谈平衡是海市蜃楼,塌陷只是时间问题。
倒车、仰视长镜头、弦乐停落。
男主巧是人类悲剧性的一个缩影,一方面,人类处处谈动物共生,与动物相处中透露出渴求平等、交流的动物性渴求;另一方面,人类成为人后,没办法脱离社会性的囹圄,城市建设、邻里关系、为族群谋利益。
他在自然和社会之间选择了抑压,拒绝明确地站在一方的立场(比如像村民年轻人选择了站在自然一方,至少意志上要与现代社会为敌,这就逃离了这种矛盾)。
影片开初有一种纪录片的感觉,一切都好像自然发生,没有经过编排,结局却极具《夜以继日》《欢乐时光》式的戏剧效果。
沿用欢乐时光中的三名素人演员。
片尾的夜雾升起,野鹿消失,好似一场梦。
邪恶不存在,巧的杀人可能就是一种选择,跟被侵占了生存空间的鹿对人的杀意一样。
@HK AFF2023
7 ) “这种 ‘犹豫’的想法就是电影”
一些Facts:1. 影片作曲者是石桥英子,她也是滨口龙介前作《驾驶我的车》的作曲者。
2. 本片创作起源:拍摄《驾驶我的车》时,石桥英子要求制作组为一个现场音乐表演拍一些镜头,最后这些镜头组成了无对白80分钟影片《馈赠》(2023年10月于根特电影节上映,石桥英子现场配乐)。
之后,滨口龙介想更进一步,征得许可后将这个项目扩展为现在的《邪恶不存在》。
3. 滨口龙介:“我某种程度上也希望人们对结局保有某些犹豫。
这种 ‘犹豫’的想法就是电影。
”4. 滨口龙介:“角色的行动并不是出于伦理的考虑,而是直觉。
”以下内容涉及剧透影片于大量空镜头和配乐之上开始构建,了解这一特殊的源起是进入影片的前提。
我们多次注意到在用平移镜头展现密林时,音乐戛然而止,紧随其后的是人物与人声的出现,再之后,视点由自然景观转移到人。
由此,人始终成为影片中的介入者和破坏者——即使他们是这里的居民,和自然共存着。
资本的商业企图作为影片的明线,明晃晃地亮着刺刀,悬挂对这片密林的威胁,实则这块幕布早在战后第一批居民到来时就已经开始被刺穿。
公司代表对于居民来说是外来者和侵入者,而对于自然来说,这些居民也同样如此。
居民虽然居住于乡村,但生活方式和文化环境依然是现代的,他们也弹大键琴,也开汽车,也有精致的现代餐桌用具,他们是介于自然和都市的灰色人群。
在空镜头之余,有两段密集的讨论片段,这是滨口龙介的拿手好戏,也是他赋予人物信念感、利用对话和节奏表现人物的重要方式。
第一段的对话中,分野了两个阵营,在影片语境下是“正义”和“邪恶”的两方。
“正义”一方的真切顾虑在“邪恶”一方的和稀泥处理方式下似乎显得无助且悲壮,观众的情感立场自然也不言而明。
而在第二段两位公司代表的车内对话中,精彩的打趣快速丰满了他们的形象,他们不再是一个邪恶的符号,而当他们也逐渐倾向到居民和自然一方时,他们显得如此可爱,他们的邪恶似乎不再存在。
这是影片轻松且易于接受的一次转折和颠覆。
就在观众和角色即将形成“邪恶”不存在的共识时,那把明晃晃的刺刀在客观上依然高悬,而影片极速进行了又一次颠覆性的转折:“正义”如爆炸一般露出了狰狞的“邪恶”。
作为最引人争议的片段,它无疑是会在第一时间激怒观众的——它打破了观众从一开始就持续的共识,崩解了人们对“与自然和谐共处的人”的想象,但影片又完全无意于安抚,更似挑衅式地结束了。
不同于此前给足理由和过渡的转变,这次的巨大转折对观众来说极具破坏性。
创作者将结尾剧情呈现得模糊又抽象,无论如何猜测剖析鹿和拓海父女的动机和隐喻,无论如何努力地试图还原事件的真实经过,都很大程度上只能是个人意淫。
不管是简单的还是复杂的解读都是不恰当的,这正如滨口龙介本人所说,怀疑就是这场戏的目的之一。
影片真正想表达的是,任何判断都存在着灰色阴影,貌似美好的都存在蛰伏的危机(猎枪声、路边尸骨、有倒刺的植物),而乍现的邪恶也存在留白。
以拓海为代表的这批居民在此刻也真正共识性地滑入“正义”与“邪恶”之间的灰色地带。
“邪恶不存在”是影片收束点之前的共识,之后的颠覆时刻最大的意图就在于颠覆本身,而非逻辑和说教,所以过度的剖析总显得单薄,那些“为什么”的问题需要观众离开影厅后在漫长的生活中自己找到自己的答案,这是电影能带给我们的财富。
滨口龙介较早期影片(《欢乐时光》、《夜以继日》)和近期影片的节奏和氛围有很大不同:早期相当松弛,而近期相比起来更加紧绷(尤其是《驾驶我的车》)。
《邪恶不存在》是滨口龙介再次回到早期风格的实践,最与之相似的就是《欢乐时光》,我们可以看到很多这部317分钟超长作的影子——乌冬面夫妇和女性公司代表都是《欢乐时光》的演员回归出演(并且他们都是素人),摄影北川喜雄也是《欢乐时光》之后首次回归参与滨口龙介电影的摄影。
而在《欢乐时光》和《夜以继日》中,角色直觉性的行为往往是电影的重要符号,是巨大转折的发动机,它们通常也令观众感到不可思议,这也是滨口龙介的创作特点——角色会直接表现他们内心的冲动,即使它有悖伦理和常规。
在接受了这一点后,拓海最后出乎意料的行动也为这部电影烙下了滨口龙介标志性的印记,它是滨口龙介风格的体现,无论你喜欢与否。
影片大方承认和揭露人的阴暗面(甚至是充斥着暴力的阴暗面),这一点贯穿滨口龙介的所有电影,似乎像是他镜头下角色的信念感来源,同样的特征沿袭自他的老师黑泽清。
黑泽清的代表作之一《X圣治》同样揭露着人内心的恶,讲述着“看起来不像杀人犯的人才最有可能杀人”的故事,黑泽清还说:“无论你如何解释电影,我不相信一部电影只限于它的开始和结束。
在那之前和之后,都有一个属于它的世界。
我想让观众感受到这部电影(《X圣治》)带给他们的除了恐怖感,还有别的可以思考的东西。
”在理解了他们师徒二人的创作哲学后,或许你会更喜欢《邪恶不存在》。
采访参考:滨口龙介∶我的团队加起来也就十个人左右(邪恶不存在)影评 (douban.com)【译】黑泽清谈犯罪杰作《X圣治》(X圣治)影评 (douban.com)
8 ) 滨口龙介∶我的团队加起来也就十个人左右
本届澳门亚欧青年电影展一场热门的大师班在澳门英皇戏院进行,滨口龙介导演亲临现场,诺大影厅座无虚席。
有缘分的是,抛开书本曾分别在74届戛纳国际电影节和71届柏林国际电影节专访过导演两回。
滨口龙介导演在影展现场,针对自己的创作历程、个人影像风格、创作经验进行了详细的分享。
以下是大师班现场对谈实录整理:
速记:1900 妖妖审阅:刘小黛策划:抛开书本编辑部梁洛施:大家好,我是亚欧青年电影展的形象大使梁洛施,早上好。
他25岁开始拍电影,2003年拍摄了8mm电影《若无其事的样子》(Like Nothing Happened),2008年编导了电影《激情》(Passion),2010自编自导了电影《景深》(The Depths),2012年自编自导了电影《亲密》(Intimacies),2013年执导了短片《触不到的肌肤》(Touching the Skin of Eeriness),2015年自编自导了电影《欢乐时光》(Happy Hour),这部318分钟的电影获得了第68届洛迦诺国际电影节特别提及奖。
2018年他执导了爱情电影《夜以继日》(Asako I&II)获得了第71届戛纳国际电影节金棕榈奖提名。
2021年7月凭借《驾驶我的车》(Drive My Car)获得第74届戛纳国际电影节主竞赛单元最佳编剧,2022年凭借同一部影片获得奥斯卡最佳国际影片。
2023年,他的新片《邪恶不存在》获得第80届威尼斯电影节银狮评委会大奖。
他就是今天的大师滨口龙介导演。
滨口龙介:大家好(中文),非常感谢大家到来,我看到来了很多人,我非常感动。
主持人:您的电影中,讨论自我和他者的关系常常涉及道德性,您怎么看待自我与他人之间伦理的关系?
滨口龙介:我在来之前看了主持人的问题,不知道能不能全部回答上来。
我考虑自己与他人之间的关系,在电影中表现为摄影机与演员之间的关系。
我是在摄影机后面的人,对我来说,问题是要让摄影机之前的人展现给我内心的确信感。
我知道让对方展现这样的东西是很困难的,所以我要让那个被摄体有一种安心的状态。
然而,问题是,我们都知道,那个被摄体把他的内核展现给我,实际上是展现给了所有的观众,所以我们不可能让那个人百分之百安心。
我在写剧本的时候,需要确保台词是能说出来的,同时,作为创作者,我需要考虑如何把自己的东西表达出来,所以这是一种平衡。
当我打破这种平衡,会变成对我的一种暴力或者对他者的一种暴力。
我也在不停地探索如何做得更好。
幸运的是通常从结果上来讲,摄影机后面和摄影机前面的人做出的平衡是好的。
摄影机前后的关系就是您刚才说的自我和他人之间的关系。
主持人:自我和他者的关系,一层是作为电影创作者,您与摄影机前人物的关系,另一种就是电影中人物之间的关系。
滨口龙介:关于这个点,我知道自己受到很多电影创作者的影响,但这与我的性格也有很大的关系。
在一般人看来,导演有绝对权力,王者一般的地位,我之前也想过自己是否要成为这样的角色,觉得我也要成为一个王者,有绝对的说服力,但是最后我还是做不到,因为我害怕如果我非常强势,对方也会非常强势地对我或者无视我。
如果他这样做了,我会觉得是我的问题。
这是我自身性格所致,我无法改变,但我觉得这样也挺好的。
当然随着我的年纪增长,对别人的顾虑也减少了,慢慢从其他导演那里学到,对他人可以强势一点。
但好像也不一定需要那样做。
主持人:您的电影中,有种特殊的关系,是艺术家和他人之间的关系,是什么让你选择呈现这样的关系呢。
滨口龙介:确实有很多人指出我电影中艺术家常常出现,也有很多解释,但我其实没有想那么多。
就是自然而然的放进去了。
当然有一个重要的原因是,早期我没有钱,所以我的美术不能做得很完美,所以不能拍特别大的场景。
既然客观条件有限制,唯一能做的就是让我的人物更丰富,所以会出现戏剧之类的形式。
这是我电影中出现艺术家的原因。
对我来说这是社会中正常出现的事情。
当然社会中不只有艺术家,还有别样的人,但我觉得如果我连这个都拍不好,那我也不能拍好社会。
我作品中的艺术家会有很多的身体劳动,就非常单纯地表现他们会做什么事。
这个过程中,我会对演员进行一定的训练,信息量会慢慢增加。
主持人:在电影《邪恶不存在》中,也有自我与他者的邂逅,最后也有一个暴力悲剧的结局。
我觉得您作品中有一种暴力的暗流,这让我想到黑泽清导演。
您师从黑泽清导演,从他身上学到了什么?
滨口龙介:如果您让我说从他身上学到什么,我觉得一个小时也说不完。
大家看过《X圣治》(Cure,1997)这部电影吗?
(现场举手寥寥几人)我觉得这是20世纪最伟大的作品之一。
《X圣治》海报我给大家简单介绍一下这部电影。
电影中,凶手每杀一个人都会留下一个X的印记;人们内心的恶被一种催眠术诱导出来。
主人公本来是个警察,但是在调查这件事的时候也慢慢地被催眠。
这部电影很有趣,同时也很恐怖。
看到一个非常普通的人身上发生那样的事情,会让我们想到自己,想到我身上会不会也发生。
我们经常会看到电视中报道这种杀人案件,从表面上看不出来凶手会做这样的事情。
黑泽清说,看起来不像杀人犯的人才最有可能杀人。
我觉得这是黑泽清的哲学。
好人和坏人之间的界限是很模糊的。
我也不能说得太准确,但我从他身上学到了这些。
您刚才提到的暗流就是人的阴暗面。
与其说我在黑泽清身上学到了什么,也是我在他作品中学到的。
希望大家在看完我的作品之后也看看我推荐的这部。
主持人:我自己也是《X圣治》的粉丝。
《邪恶不存在》也涉及社会的氛围,你觉得现在日本社会有没有改变?
滨口龙介:1995年日本发生了很重大的事(编辑按:应指奥姆真理教三大事件的最后一个,地铁沙林毒气事件),这件事导致社会发生了重大的改变。
我觉得那是仅次于二战的重大事件,到现在也在产生影响。
我甚至觉得,那件事的影响在不断扩大。
让我最震惊的是,参加这个邪教的人甚至有很多是精英人士。
日本80年代的经济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很多人无法适应,为了寻求救赎,他们跨过了准线。
类似性质的事情后来虽然已经改变了形式,但我认为仍然在持续。
日本人不太会同时信仰多个宗教,我们有个共同意识就是宗教是比较可怕的,害怕自己被强加高于社会准则的东西。
我自己是一个无神论者,日本社会在宗教和资本主义的两重影响下,很多人的内心没有得到满足,这种饥渴日渐强烈,导致了很多社会事件的发生。
主持人:《邪恶不存在》的结局反映了真实社会。
滨口龙介:自己是没有这样的想法的。
作为生活在社会当中的个体,我会产生一些思考,但我没有刻意反映到我的剧本当中。
我只会考虑人物的特性,考虑角色应该说什么话。
《邪恶不存在》的结局,很多人问我是否没有写完,但这个就是我设想的结局。
角色的行动并不是出于伦理的考虑,而是直觉。
我对于自己创作的这个结局有强烈的确信感,主角也很好地表达出来了。
用言语和身体不能表达的感觉,我都表达在了影像中。
主持人:《邪恶不存在》这个演员也是你的团队的一员。
滨口龙介:是的,他在《偶然与想象》中是工作人员,在《邪恶不存在》中是主演。
主持人:《邪恶不存在》在我看来,视觉感觉非常强烈,也许是因为大部分的场景都在户外。
您以往的作品可能室内比较多。
邪恶不存在中有很多森林,这里有特别构思吗?
滨口龙介:背景中有很多户外镜头,我的想法其实自然拍摄,没有太多设计。
电影是运动的影像,所以运动才是最有魅力的。
但是动起来要花钱,所以我就去找自然而然会动的东西放在电影中,这也是一种方法。
结果而言,就是户外镜头。
但《邪恶不存在》可能有些不同。
音乐是石桥英子女士提供的,她来找我做演出音乐影像,这个是作品的出发点。
我在《驾驶我的车》中与她有过合作。
我觉得她的音乐有一种纤细感,根据这个创作了《邪恶不存在》。
我们一起创作,最先出来的就是《邪恶不存在》的第一个镜头,十分钟的长镜头,那些树木都是在视觉上有渐进的。
那一片树林给我的印象与石桥英子的音乐联系了起来。
观众1:想问获奖成名对您的生活和创作有什么影响吗?
滨口龙介:我其实也没有那么有名啦,我做的也并不是主流商业片。
虽然说《驾驶我的车》卖得比较好,但也是比较罕见的。
获得奥斯卡之后有一阵搭地铁确实有人和我搭讪,但是过了一段时间就没有了,最终也没有什么变化。
观众2:您的新片感觉和之前的片子有很大不同,主题更大。
主题上面的变化是您刻意做的改变吗?
滨口龙介:我能理解您的想法,我觉得这和我刚才说的这部作品的起源有一定的关系。
我之前的创作是没有办法给石桥英子做的。
当然我也想有一些变化,这是很愉快的。
会有一些人问我,你拍这个电影是不是很愤怒?
其实没有。
观众3:您的作品中交流很重要,但新片中好像比较少。
想问下您创作的这个转变是从何开始的?
滨口龙介:听到您说交流是我作品很重要的元素,我很讶异。
我没有刻意追求,就是自然地拍摄人的状态。
这部作品我有做一些改变,但我不记得我拍摄过很沟通很顺畅的片子,因为沟通不顺畅也是我们社会的现状。
《邪恶不存在》主人公话确实比较少。
观众4:您拍摄高成本与低成本的片子感受上有什么区别?
滨口龙介: 最直观的感受就是人数的多少。
高成本的片子沟通上可能会更复杂。
其实我的片子通常所有人加起来也就十个左右,沟通起来比较顺畅,给我一种小家庭的感觉。
人员比较多的时候,可能会划分很多的部门,我作为一个导演要成为各个部门的领导者。
我也不是说觉得自己不适合拍大制作,多人的团队能产生更震撼观众的影像,这也是好事。
我会更多考虑作品的完成度。
观众5:《邪恶不存在》和《驾驶我的车》结尾都有对一些东西的揭露,是您的创作习惯吗?
《偶然与想象》有三个部分,您的创作顺序是什么?
您最喜欢哪个部分?
滨口龙介:暧昧这个东西是我作品中非常重要的元素,因为我觉得这能刺激观众的想象。
电影当中的“迷”能勾起观众的兴趣,吸引他们。
但是我不能单纯把“迷”作为一个诱饵,这样会破坏我和观众的信任关系。
所以我觉得很重要的是在一定程度上揭露但又留有一定的暧昧。
这个是我想要的状态。
《偶然与想象》我就是按照成片的顺序写的,写故事只能这样写。
如果我把顺序倒过来,我也会很好奇观众的反应,因为我觉得每一个段落都有自己相应的职能。
观众6:我看过《驾驶我的车》纪录片。
您作为导演一直在摄影机前而不是之后。
您还有这样的习惯吗?
近距离指导演员。
滨口龙介:我近十年已经不太这样做了。
拍摄之前我会非常细致地指导演员,会让他们围读剧本。
拍摄时我会大致告诉演员我想要的,然后将表演信任地交给他们。
观众7:您创作剧本有什么习惯吗?
《邪恶不存在》中音乐的戛然而止是设计吗?
有什么意图?
滨口龙介:我觉得我至今没有找到特定地创作剧本方法,有原作通常会轻松一点。
但能够拍摄的原作也没有很多,不能有太多期待。
在积累的过程中,剧本自然而然地就成形了,但什么时候完全成形没有明确的答案。
如果你有好的答案的话也请教教我。
9 ) 声音&影像
《安娜四个夜晚》&《邪恶不存在》想把这两部放一起写评价还是比较偶然的。
一是一直以来想认真写一写Skolimowski电影中的声音元素,二是看了《邪恶不存在》后偶然发现滨口也在快速进行一个从以对白到以声音+影像为主体的改变;就想大致写下一些短时记忆点,帮助之后(希望申请结束后能找寻到时间)长评打下基础。
运用戈达尔的话说,我是在为之后的长评写电影剧本。
Skolimowski给我的第一次震颤源于“EO”,看到EO是在听到turangalila symphony现场后不久;但其令我对声音认知的改变却远远大过后者。
原因大体是:首先,Skoli将梅西安想用音乐表现出的色彩投射到了屏幕上,再使用高速运动的放映机快速或慢速地移动影像;以呈现一种听觉-视觉,甚至听觉-视觉-感觉的双/三重观感。
当然,skoli那里的音乐复杂度远远不如梅西安,仅仅停留在Ligeti的微分呓语(或Cage的噪音序列)罢了。
不过,很难想象未来有人可以凭戏院屏幕这一媒介,以skoli的方式及类似的完成度,表现更复杂的音乐,例如B.A.Zimmermann(Skoli其实尝试过他,但不尽成功);或许我们得求助AR/VR。
Back to Skoli,不得不说,他不是1st tier的导演;对我而言他几乎唯一的亮点只是上述所言。
当然在《沉默的怒吼》中有其他值得说的,例如skoli如何利用80年代的“当代影像”复活被禁止的“档案影像”;也可以直接说,如何用影像唤醒另一影像。
这点亦非常有趣,可惜也只是妙手偶得。
(当然,你也很难指望一个导演一直在复活他之前的影像吧...)为何将《和安娜的四个晚上》单独拎出来说?
Skoli在之前,以及之后的电影中,大多是用快速移动的交通工具来激活影像。
早期其最喜欢拍的车祸(或载具的突然停止/启动),类似于引发炸药,将过去残留的画面一笔带过的同时开启了崭新的空间。
以及晚期《必要的杀戮》以及EO中的直升机/无人机的低空“掠摄”(掠食+摄影)。
但在“安娜”中,所有的交通工具均来自画外,指示交通工具的噪音亦在不断在撕扯着画面;主角成为了一个完全被动的个体,被虚拟的配音控制,同时被随时可能出现的、来自现实的噪音而恐吓。
主角的”四个晚上“均是在安娜的房间,这一同时拥有着逼仄的物体空间以及宽阔且空白的声音空间之场域中度过的;其成为了一个纯粹的声音感受者及调查者。
不过,要说最容易被注意到的声音+影像,自然还是飞行物在低空的“掠摄”。
《必要的杀戮》开始那段低空镜头极度有趣,特别是男主被击晕后,绕着男主三重旋转的“掠摄”。
一开始的想法是将这三重加以分级,但发现似乎将哪一重算作第一重都是情有可原的,而从哪一重开始描述又似乎不够公平;但纯粹的文字又必须分前后(或许可以搞个啥拓扑图形,留待后人吧),敬请读者公平看待以下三重“掠摄”:——离男主最近的,从外围向内部聚集的,由于直升机绕男主旋转而被吹向男主的沙子。
影片中呈流体状。
似有突出男主位置,以及增添画面多样性之功用;——也在画面中的,以固定角速度围绕穆斯林男主旋转的美军直升机。
是不断流向画面中央之沙子的推动力,同时也让观众感受到了画面本身旋转的可能性;——无人机(或是另一架直升机)拖着摄像机,绕着前两重“掠摄”以不同角速度旋转所拍摄下的镜头本身。
由于美军直升机正在旋转,这一画面本体的大幅度旋转得以成立。
而这一维度的加入,令此镜头相比起安哲某个固定视角,直升机围绕偷渡船旋转的镜头多了一重观赏乐趣。
————————————————————滨口在《邪恶不存在》中对配乐的应用过于生硬。
有趣的是,《邪》和EO及Essential Killing中有极为类似的镜头。
前者使用音乐家石桥英子的一段较长的,亦当代亦古典的配乐;搭配各类fancy却毫无内容的长镜头。
Skoli则是用Ligeti式音色及不应在影院中出现的音响强度,搭配过饱和,甚至加红色滤镜的“掠摄”镜头。
前者对配乐的应用令我想起了“Undine”中缠绵的巴赫,或者洪常秀时常用以贯穿全片的某个浪漫主义室内乐的动机。
此时音乐同影像几近完全抽离,更似一种“氛围乐”。
或者,我们也可以极端一些:此类利用了“氛围乐”贯穿全片的电影之意义,仅仅只在于为观众提供了一个此“氛围乐”的预告,或潜意识。
这样一来,观众在之后听起巴赫,就能想起他们当时“Undine”中所感受到的情绪。
情况在《邪》里稍显复杂,但类型是大致相同的。
一是滨口并没有使用大众熟悉的配乐类型;二是这样一个“动机/氛围乐”时间长,形象突出。
《邪》的音乐使用是间于skoli同《独自在夜晚的海边》/“Undine”之间的。
从早期浪漫风格出发(舒伯特),无缝隙地转向了Ligeti;似乎是预示着大自然及人类社会间的平衡将在不经意间被改变。
但并不一定是“由好变坏”,而是类似影片末尾这样“一波三折”的权力网络转换:无形的枪声——受伤的鹿——似死似活的女孩——丛林保护人/谋杀者的父亲——丛林“加害者”/被害者/由活转向死的‘外来人‘(这里我偷懒,直接将主要元素并列在一起;这部电影应需要一个很大的网络及复杂的拓扑关系才能将所有形象拼合在一起)滨口的人物关系从来不会如同是枝裕和一般。
后者只是在一个缓慢被揭示的形象上轻微波动;而前者确是一个充斥着言语(《邪》之前几乎所有长片),或我现在还难以解释的“声音——影像”的混沌系统中(即是《邪》)演变。
滨口这一尝试是极为冒险的,敢于从其熟稔的对白式电影中迈出巨大一步。
虽然《邪》对我而言完成度并不是很高,但确已足以作为样本分析。
10 ) 理性发展至此也就到头了罢
开始你以为看到了人类近乎完美的“自发秩序”,直到人人都按因果规律表达诉求,有人关心水、有人关心火…像是力求呈现多元的“无知之幕”,却都是大一统的主体视角。
给全片递上了一份极冷静的哀伤:人类理性发展至此也就到头了罢…而野鹿、孩童、原住民的共通意象是“生命本能”:野鹿敏感藏匿并不向人解释为什么需要那片森林,但受到攻击就会残喘回击;孩童在情感受到冷落时只会用脚踹表达被忽视;时间刻度也本不属于原住民的生命范畴里因此常常健忘…太多人在按着范式阐述各种理由的同时容易忘却这种生命本能,微弱如鹿如童。
只有突然的死亡与攻击才是来自自然秩序的最后解答——错拿事实判断强行干预价值判断,有些事情从开始就不需要理由。
那场沟通会只是展示了理性也能开出恶之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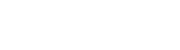











































这部并不好 整个故事不好 但是摄影和配乐真的好, 从寻人开始 到找到 中间是不是跳过了100集没拍?然后直接给我们一个结尾....
@@(2023-09-04)悪は存在しない(Evil Does Not Exist)(邪恶不存在)(不知所云的闷片。或许是在说,村民觉得外来开发者破坏他们的生产生活方式是邪恶的,但对于当地生灵来说村民也是外来开发者、也是邪恶的,所以邪恶无处不在,所以邪恶不存在。)
在静谧倾听的自然里,敏感弥散在空气中,一粒外来的石子,不论善恶,都会在此处荡开涟漪。
@电影资料馆。终于有展现可恶glamping的作品出现了!可是,为什么村民比露营公司职员看上去更像glamping呢——露营公司打算聘男主角作顾问,正如这群新一代村民视村长为mentor一样(为酋长献上羽毛!)(“这野山葵以前的饭店有哦”)。整体比较陈腔滥调,比如主角深沉的“大森林之子”人设;饭馆女厨在发布会上近乎神经病似的“真诚”人设;结尾莫名其妙的功能性扭打…… 闷热的影院里充满了乖巧的笑声。
#VIFF2023 后劲十足,滨口的大师气象已经完全成型,而且跟当下日本某热点议题形成了微妙的互文。剧本严丝合缝到让人怀疑他是否有强迫症:以“城市”为分界,所有前半段的“无聊”都变成后半段收回的伏笔,众多群像寥寥几笔就能让人完全记住。迷惑的结尾其实是神话传说式的处理,开头小女孩灵动的入镜对照最后的内伤和父亲的喘息声,还有善良女员工与虚伪男员工截然不同的下场,使得“鹿神”与“守护人”的关系呼之欲出。唯一败笔是过满的配乐,以他前作风格和对情节强度的把控能力,基本只需一头一尾渲染神性即可,中间数次的戛然而止反而暴露了赶工的粗糙。但整体而言依然是年度佳作,且在各种节展流行用“奇技淫巧”来取悦评委和观众的当下更显得难能可贵。
3.5 若黑澤清在《超凡神樹》透過因鏡頭、情節、信息的留白和割裂而持續增生的神秘感,驅散縈繞神樹之外的各種意義或闡釋,藉由符號性死亡還原其本真性,那濱口在本片也在進行類似嘗試:室外的環境描寫,與室內/車內的世俗對話構成潛在衝突。建立自然的法則,須同時堅拒加諸其上的抒情、美化與詆譭,即剝離一切外部意義,包括支撐人類社會運作的道德性。無論兩場會議體現的資本與平民、外來與本土的角力;員工閒話家常;女孩探尋自然;還是隱約的槍聲和死鹿,無一不引向挫折和徒勞。秘密、真相不關於對這些意義的表述歸納,而僅僅遵循一個「簡單」的邏輯:讓道德服膺自然的秩序,超越善惡後,逐漸顯露的真實。跟隨游移的視點,「非人」的車尾鏡頭留下的蹤跡,最終走向(回)濃霧瀰漫、枝枒蔓生的森林:在那裡,邪惡並不存在,或是屬於自然的「惡」。
人对自身所作所为造成的恶果毫不知情。恶好似蝴蝶效应,邪不总是初衷。本是值得深思且与时俱进的主题,却靠操纵小孩来教育大人。小孩变成木偶,人与自然冥冥之中的连结使人难以信服,意欲大胆、富有留白的结尾也牵强附会,冷酷但并不一定就有深意。以失败的人物关系塑造(尤其父女)强迫对自然的敬畏之心。我喜欢它的现代性和幽默感,在这一层面我觉得滨口的创作有所进步,但对议题的把握和呈现上太机关算尽和讨好电影节了。表达主观真实和表态客观真理有时只能重其一,想play safe又想impress,你感觉它绕来绕去,缺乏向前的决断,目的却欲盖弥彰;准确说这是一部姿态很满,却缺乏作者个人声音的电影。大自然没有感情(北野武说的)可是音乐有感情。这个片子的音乐着实为赋新词强说愁。感谢bfi的£0电影票
SIFF2024 只能说这片子反映出环保议题在虚构剧情片中确实比较棘手,关键就在于不能只把它作为引子或幌子,因为它直接关涉到影片的空间建构和景观呈现是否可信。对比怀斯曼很多涉及社区自治的纪录片(小A短评也贴出了日本建设项目的正规流程可能是什么),影片中的营地项目语焉不详,村民和开发商的矛盾也比较简单直白,“为了碟醋包饺子”感过于强烈。倘若先给予环保议题真诚且充分的讨论,再从这个话题的孔隙中自然生长出对于后疫情时代生存状态的思考,就会好很多,并不是说只能拍成纪录片,但确实也更难把握平衡。滨口的舒适区显然是那场男女车上的对话,这其实会是一个很好的衔接和转捩点,但目前看来只是不痛不痒的点缀罢了。
好有意思,一开始以为也是毫无作用、自我感动的文艺风光片,看到中段完全明白前面每一秒都是有用的,看到小村的日常、与自然的关系尤其是身处其中人们的节奏是至关重要的,所以当外人也来重做一遍片头的事时,那种试图融入的僵硬确实显得又笨拙又真诚。结尾的时空交错可以说非常直白了,但这样做又有浪漫所在,显得非常超乎现实,结合了这些人的性格又觉得合理。作为一个本职就做文旅项目的人,简直对其中冷漠的现实和种种人性的荒谬的复杂纠缠太有体会,简直是我的职业引述片。细腻、柔软、清澈又有强烈的悬疑和冰冷的暴力,感觉片儿很短就看完了。爸爸背着女孩那段好舒适,与自然达成平衡交易的人生,如果你也有这样的意愿那可以看看这片儿。放下高傲、急躁,用开放的心态,给自己一个不到2小时的假期。
也是为了拿经费拍的?
#FoyCAE#很符合大时代环保潮流。人与动物的博弈。大师班现场,滨口说音乐是石桥英子女士提供的,她来找导演做演出音乐影像,这个是作品的出发点。影像完全匹配音乐进行叙事,内核残酷,视听很享受。
在《驾驶我的车》大获全胜之后,滨口龙介尝试彻底拥抱大教堂的政治正确,并完成一部ecocinema,但正如同片名暴露出了影片的问题:邪恶不存在,暗黑生态学也不存在,滨口没有向他的导师黑泽清在《光明的未来》或《超凡神树》,通过怪异的物体的存在或量积引发可能的末世感,也并非如图河濑直美,将摄影机运动生成为神隐的少女ハナ的幽灵视,相反,即便导演使用了更多的自然景观的空镜头,却始终处于一个外部的,人类/城市中心的,舞台调度的观看视角;甚至就连“消失”本身也是对于导演之前《夜以继日》的弱化版重复,影片唯一的精彩段落在于开发公司的两位职员回到城市的视频通话,以及在返归村庄进行协商之时漫长的车内对白,只有这些才能提醒观看者这部影片出自滨口龙介之手,但它却是与全片最为无关的,悬浮性质的段落。
#2024BJIFF#我脑海里实在想不出什么赞美之词,在我看来是一部严重过誉之作。滨口龙介采用了非线性叙事手法,尽力去表达邪恶并非停留在犯罪或暴力,而是深藏于每个人心中的议题。台词写的极度无聊,全片零碎又缓慢的叙事,全程令人昏昏欲睡,全场结束无一人掌声,恕我欣赏不来。
他呀没有你难看呐,你呀比他难看呐。
4.0。北大百讲戴锦华教授导赏。1.戴老师自家主场要比其它场合说得多和细,区别于其它一切自然生态环保片,滨口龙介企图通过恶的“突如其来”回扣他一以贯之的自我和他者的创作母题。2.外来作为“大他者”反作用于主体,使其邪恶附体(突然的枪声、妻子的不在场、男职员随意的态度以及弹矢后具有伤害性的鹿),完成由外而内的转换。3.延续老师黑泽清“大他者”般的幽灵视点。
要不你赔我点钱吧。
#SGIFF#节奏依然格外缓慢,摄影格外好,结局很震惊,但是完全无法理解,滨口龙介真不是我的菜。
陷入思考 ∵若说“自然”和“人类”之间并没有绝对界限 即说无情和有情众生之间也没有 自然界中无善恶 人间也没有 ∴邪恶不存在 。如海啸 如雪崩 如鹿中枪 如手划伤 。
好低的成本,好高级的叙事,好长的镜头,好猝不及防的结尾
结局没有任何必要。邪恶也许不在角色身上,但绝对在从头到尾对角色怀着恶意的导演身上。像是兰斯莫斯恶意篡改的滨口龙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