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能召回前世的布米叔叔》剧情介绍
布米叔叔(Thanapat Saisaymar 饰)得了急性肾衰竭,因此回到乡里,边静养边等待死神来临。在乡下,他每天安静的吃饭、纳凉、看家人劳作,一个清凉的夏夜,布米叔叔、侄子和妻妹在院子里吃饭闲聊,布米叔叔去世很久的妻子竟然出现了,和他们诉说近况和多年思念,稍后,布 米叔叔失踪很久的儿子也出现了,变成了一只红眼黑毛猩猩,却没有人受到惊吓。阴阳相隔的几个人平静地拉着家常,平静的果园,平静的微风,蜜蜂每日平静的劳作,发生的一切事情都那么自然,每个风景都早在那里了,每个故事都像一个梦…… 本片获戛纳电影节金棕榈大奖。热播电视剧最新电影知法犯法暗金丑岛君:完结篇圣山恐惧有限公司机器人之梦封魔纪之杨戬传情人节恋事幸运钥匙最后的日子利勒哈默尔第二季从最尽头徒步5分钟封神之人鱼传说台北过手无暝无日养鬼吃人9:启示录美国谍梦第五季黑吃黑第四季黑岩射手火红年代暗地深仇判我有罪下一站你的世界爱斗大怒海劫运火凤凰我可能不会爱你保罗·好莱坞的欧陆公路之旅第一季如果她的旗帜被折断了超能查派开战日真命天子
《能召回前世的布米叔叔》长篇影评
1 ) 苎萝人去,蓬莱山在,老树荒碑。
两首词的意象,与电影的意象有极高的相似性。
其一:《人月圆 ·会稽怀古·北曲聊乐府前集今》——张可久林深藏却云门寺,回首若耶溪。
苎萝人去,蓬莱山在,老树荒碑。
神仙何处,烧丹傍井,试墨临池。
荷花十里,清风鉴水,明月天衣。
其二:“虽年百岁,犹若刹那,如东逝之长波,似西垂之残照,击石之星火,骤隙之迅驹,风里之微灯。
草头之悬露。
临崖之朽树,烁目之电光。
”——《宗镜录》是为记。
2 ) 《记忆前世的人》:阿彼察邦创造另外一个宇宙
在千禧年第一个十年里,泰国导演阿彼察邦无疑是全世界最被瞩目的导演之一。
他自2000年开始电影历程,他的第二部电影、2002年拍摄的《你的幸福》获得了当年的戛纳电影节特别关注奖,2004年的《热带疾病》则获得了戛纳电影节评审团奖,他的上一部电影《综合症与一百年》入围第63届威尼斯电影节。
他备受法国《电影手册》推崇,今年年初,他的《热带疾病》入围其评选的“新千年十佳电影”。
又一个十年开端之际的戛纳电影节,显得过于平淡。
哪怕大师出手也并不惊人,新人登场也不显生猛,但好在阿彼察邦出现了。
在中国电影尚在争论电影与票房,电影要讲一个好故事,应该成为解压最好的娱乐手段的时候,和试图做更深入的哲学探讨,表达人本身所在与需求的世界电影拉开了数以光年计的距离。
甚至,有的强大的作者,一直在创造另外一个宇宙,观众只是好奇或不解的他者。
阿彼察邦就是这样一个强大的作者,他出生于1970年,和中国导演贾樟柯出生于相同的年份。
二人在美学追求、处境、历程、在世界影坛的位置有七分相似,他们都有美术功底,对于电影中的空间呈现情有独钟,也都有挥之不去的故乡情怀。
他们之所以能够在世界影坛占有一席之地,不光是因为电影讲述的内容,更重要的是他们电影的表现形式和结构。
他们是真正具当代性的导演,早已不将电影着眼于确切观点的表达。
二人不同的地方在于,一个企图走向体制内部,去改变体制,一个仍然积极地与体制唱着反调。
2007年,阿彼察邦曾发表过一封致泰国政府的公开信,因为他的电影《综合症与一百年》没有通过泰国相关机构的审查,无法在泰国国内上映。
他在信里这样表述,“我,一个电影工作者,把我的作品当作自己的儿女。
在我孕育他们的时候,他们就有了自主的生命。
既然我已竭尽所能地创造了他们,故尔,我并不在乎别人是否喜欢或者讨厌他们。
无论什么原因,如果我的后代无法在自己的国家生活,那么就给他们自由吧。
在这个世界上,有很多地方会因为他们是谁而热烈地欢迎他们的。
我不能因为害怕制度,或者为了牟利,而去残害我的儿女。
否则,无法继续艺术创作。
”随后,他发起了“自由泰国电影运动”,得到了全球电影人的联合签名支持。
在这封公开信里,他表达了自己以自我为原则创造电影的宗旨,他的创作并不受其他因素,比如票房,观众的喜欢,影评人的偏好,电影节的认可……的影响,甚至开启了一种犀利、新鲜的电影语言。
《记忆前世的人》就是这样一部电影,呈现出导演自身对于人类和其他动物的关系,灵魂的转移,物种的毁灭,信仰的独裁等观念的思考,也是向现行的泰国电影审查制度宣战的又一部力作。
上一届的戛纳电影节,丹麦大师拉斯-冯-提尔的《反基督者》因其惊悚和黑暗的特质让人久久难以平静,但它是英文电影,又有西方基督教为背景,在广泛的群众基础上引起了极大争议。
《记忆前世的人》相比起来,更为复杂,但它植根于泰国原生态文化,显得更为私人,也更加哲学,因此在被理解和被接受的程度上会弱于《反基督者》。
《追忆前世的人》讲述了布米叔叔因为肾衰竭即将离开人世,他回到老家度过自己生命中的最后时光,亡妻的灵魂和他失散多年、变成了猩猩的儿子都回到了他的身边。
为了能找到自己得病的原因,布米叔叔在家人的陪伴下穿越了树林,来到了深山里的洞穴,并死在那里。
而那个洞穴则是他出生的地方,隐喻子宫。
谈及拍摄初衷,阿彼察邦称,“几年前,我遇到了布米大叔,在我家旁边寺庙的住持告诉我,庙里来了位大叔学习冥想,还帮着张罗一些庙里的活动。
有一天,布米大叔找到一位住持,告诉他当他在冥想的时候,他能够闭着双眼看到他的前世,就像看电影一样。
他看到并感受到自己是一头水牛、一头牛,甚至精神脱离躯体,在东北平原上漫步。
住持被触动,但并不感到惊讶,因为布米大叔不是第一个和他描述此类经历的人。
渐渐地,他从村里和他分享前世的人那里收集故事。
后来,他出版了一本小册子。
在封面上写道:一个能够回忆起他前世的人。
”在原先的剧本里,按照原著,详尽解释了布米大叔的前世,按照阿彼察邦说辞的推测,应该是影片开始出现的那头水牛,但他说,“在电影里,我决定尊重观众的想象。
他可以是影片里的一切生物,虫子、蜜蜂、士兵、鲶鱼什么的,他甚至可以是他像猩猩的儿子和鬼魂妻子。
”这样一来,影片加强了电影与转世的特殊联系,表达出了阿彼察邦自己对于转世的看法。
和原著相比,这部电影里有很多阿彼察邦自己的东西。
比如,在影像风格上很像他成长时期所看到的泰国电影,比如,让布米叔叔和他过世的父亲一样,都是因为肾衰竭而离开人世,比如,在布米叔叔卧室里的所有那些装置都是他父亲的原样复制。
这是一部需要反复观看,且斟酌的电影,如果它第一次震惊到你,但愿接下来的第二次、第三次,你能够穿越火线进入到这个宇宙。
新浪娱乐前方报道组发自戛纳
3 ) 枝流叶布•家于兹土
“那片土地,那块银幕,是布米叔叔的前世与我的个人记忆,交汇的地方。
他正在谈论的正是我的梦境。
这个梦关于将来,更隐射当下。
”——阿彼察邦•韦拉斯哈古文/仁直简单地说,影片讲述了一个垂死之人的弥留“片刻”。
死亡与时间,正是构成整部影片的基本骨架。
阿彼察邦砸碎了宗教故事、神话传说以及作者记忆,使得整部影片散发出一股浓烈的乡愁气息。
从这个意义上说,《布米叔叔》又是一部记忆体电影。
人性与兽性、自然与人为、生与死,电影嵌套电影(作者对自己以往影片的揶揄),光亮与黑暗,如此种种,枝对叶比,模糊一片。
阿彼察邦说道,“这部电影,好像我之前所有虚构电影的总和。
尾声,所有的角色都重新登台。
它是我对那片土地以及电影艺术的致敬。
”附在胶片上的老灵魂按照印度佛教的说法,万物是有灵的。
业(karma),梵文[羯磨]的意译,即善恶行为所留下的一种无形而有力的能。
出现在影片之中的“布米叔叔”扮演的正是这一“形而上”的诠释者。
他的妻子(鬼魂)、他的儿子(鬼猿),都可以看做他对于前世姻缘的自我投射。
阿彼察邦说道,“一头牛、一尾鱼、一束光,布米叔叔可以成为任何‘东西’。
”与此同时,阿彼察邦又对布米叔叔这个人物进行了“形而下”的指涉——一个开有私家农场的,曾为泰国政府效力的屠杀原住民的共产党人。
按照阿彼察邦的话讲,“整部电影以卷轴的方式,分为六段。
每一段都有着各自不同的表现形式——格调、打光、表演风格以及环境设定。
例如第二段的‘晚餐戏’,就与影片第一段的风格不一样,这个段落的打光方式更类似于旧电视的风格(16mm,摄影棚拍摄),光非常的硬,非常的墨守成规,总有强光打在说话人物的脸上。
到了第三段,自然光再次出现,人物跌跌跄跄地在阳光下行走。
到了第四段,影片的风格又变了,影片好像变成了一个披着华丽戏服的公主故事。
到了第五段,就只剩下丛林和洞穴了。
”笔者认为,阿彼察邦所论的六段式结构,大致可以这么分:启幕、晚餐(闪回)、农场、公主、洞穴(未来),以及和尚。
其中的第五段——“洞穴”——直接指涉了作者意欲将影片带回电影源头(子宫)的冲动。
因为,出现在这一段落的丛林,并不是“实相”,而是一种电影术的虚像——阿彼察邦利用滤镜(绿色以及蓝色),白景夜拍了这一段落。
相比而言,同样出现在《热带疾病》Tropical Malady(2004)里的丛林,无论是视觉还是概念,都与《布米叔叔》有很大的区别。
《布米叔叔》里的丛林是人造的,是一种电影化的道具密度,类同于一个角色的身份。
它带领着布米叔叔,穿越鸿宇,回到子宫。
反之,《热带疾病》里的丛林是一个“避难所”。
在那里,人类和动物都回归到了生物的状态。
所以,我们大可不必教科书一般地将《布米叔叔》定义为某类型电影。
如果非要给这部电影加个类型的话,那也只有——open cinema——适合这部电影。
它可以是恐怖片,它可以是爱情片,它可以是神怪片,它也可以是纪录片。
《Time Out London》的David Jenkins说得更为直接,“阿彼察邦并未试图通过这部电影灌输给我们什么,他只是用那些长镜头以及那些微妙的剪辑,孕育观众自己的意识构成。
”尤其是那个被阿彼察邦喻为,“死亡与时间”的结尾。
这个结尾,到底讲了什么?
如何诠释?
恐怕只有仁者见仁了。
且,现在的泰国,一方面正在进行高速的现代化建设——民主&人权;另一方面,这些笃信婆罗门的泰国人又用水桶积攒下抗议者的鲜血,唱着祈求神灵的颂歌对着首相府倾倒血桶。
从这个意义上讲,《布米叔叔》正是混杂了这种现代化的残酷以及古老传统的笃信。
说得透彻一点,阿彼察邦试图通过这部电影,唤醒现代人的“前世记忆”——寓言(Fables),老电视(Old Television),泰国小说(Novels in Thailand)。
注:影片拍摄于泰国的东北部小城Nabua。
起先,阿彼察邦对于这个地方有点格格不入。
于是,他花费了大量的时间写自己的日记。
如此一来,影片的灵感来源——“布米叔叔的故事”(一个和尚撰写的,非货架销售的小书)——变成了影片的一条支线。
阿彼察邦的个人乡愁,以及他对于往昔电影的致敬,成为了这部电影的血与骨。
4 ) 有一只飞蛾停在我的下巴上
全片最喜欢水中那段。
Narcissism的确是一种自慰体验,幻象里水中鱼尾湿润的击打,对应现实中女人寂寞地用电蚊拍驱散灯下的飞虫。
死去的爱人与走失的孩子在濒死时有了实体,在一个夜晚返归,临终前只想在爱人的怀里诉说自己最初的恐惧和被保留下来的爱意,回到子宫的洞穴,在鬼猿的注视下,将体内的液体慢慢排空,变回一颗尚未萌发的干瘪的种子。
人们常常以为宗教经验带来的是某种神圣性与崇高性,然而通常情况是,信仰用来冲淡并且将一些神秘体验合理化,给人面对不可解的事物时以支撑。
“鬼魂记得都不是地方,而是活人。
” 想起之前看到过的怪谈:飞蛾经常环绕在身边是故去的亲人的化身。
有一次美妙的体验是之前有天傍晚一只飞蛾停在我的下巴上。
“有关前世的记忆,我们在黑暗里出生,不知道自己是人还是动物 是男人还是女人。
”电影作为介质,保存的恰恰是来自过去的拟象,是前世记忆中的可能一种。
泰国电影给我和台湾电影相同的影像质感,可能和环境气候有关,但是又无法解释其中鬼气与情色结合反射着珠光的部分,不知道再看看。
5 ) 人鬼非殊途
不同与以往作品节奏的控制镜头都控制的变少大段落的描述像极了安东尼奥尼,这些都只是为了准确的讲述一个前生今世的故事多少次,我们真能有机会捧起水中的公主面容改变不过是几世的轮回灵魂一直不朽可岁月的轮转就连鬼魂也沉受不起社会的发展精神的折磨经过岁月的历练渐然都可渗透到肉体社会不变神鬼不止
6 ) 祭如在——游荡在现代的鬼神观念
看完片子,读了目前不多的几篇影评,发现大家的注意大多放在“鬼神”上。
这固然是片子浓墨重彩之处,但如果把一些看似背景性的故事情节勾连起来,不难发觉阿彼察邦并不是单纯的讲鬼神,而是试图讲述鬼神观念在泰国这个现代社会中的位置,如果只看到片子“魔幻”的一面,丢掉了“现实主义”的一面,就难免断章取义了。
举例来说,电影主人公布米叔叔的现世生命,就是靠现代医学技术肾透析来维持的,尽管是民间简陋的模仿,不是在医院进行的正规治疗,但这一技术本身无疑是现代科学的产物;布米叔叔的产业——农场,普遍使用杀虫剂,乃至他和小姨子进去的时候要戴上口罩;布米死去的儿子孜孜不倦学习的是摄影,这一把自然对象化的技艺,最终却把让他完全融于大自然,算是科学给他开的一个玩笑;珍姨在灯下扑杀蚊虫,用的是电蚊拍,这一段给了至少一分钟的长镜头,与前面她小心翼翼的注意脚下是否踩到昆虫形成鲜明对比。
此外,虽然全片渲染鬼神,生灵,轮回转世等民间宗教观念习俗,但在年轻人一代中间,这些旧有的信仰显然已经开始瓦解。
布米的侄子虽然在葬礼期间为僧,但却进入女性房间,洗澡,午后用餐,对佛门清规戒律并不在意。
片末卡拉OK传出的流行乐,更是再现代不过的玩意了。
总的来说,片中的泰国村民,对于鬼神,与其说持一种绝对的敬畏,不如说更接近孔子所说“祭如在,祭神如神在”的心态,在他们那里,鬼神观念已经和现代生活融为一体。
在我看来,阿比察邦的作品展现的是鬼神传统和现代物质生活互相包容的可能性:在布米叔叔一家眼中,韦伯那种“附魅”和“去魅”的古今之争已是荡然无存了。
7 ) 流動的饗宴
如果海明威說,年少時遇見的巴黎是一席流動的饗宴;那麼Apichatphong Weerasethakul的《波米叔叔的前世今生》則是一場帶領我們越過山林,穿梭前世今生生死輪迴的生之筵席。
有別於馬康多的從無到有,最終又灰飛煙滅回到空無;Apichatphong領著我們一同靜觀波米叔叔的人生終局,死亡之後又再度回到留下的人,彷彿生死死生是個不斷流轉的圓。
在那最後的幾晚,許多人都來了─遠房的親戚、死去多年的妻子、離散的孩子。
所有人齊聚ㄧ堂。
生、死、垂死、青年、老年、動物,共同倚著餐桌,如同一幅再寫實不過的人生風景。
沒有人因鬼魂的到來、生靈的到來而感到大驚小怪,而是平靜地好像什麼都在自然不過;沒有人談些什麼大道理、悔恨,只是細數著過往的回憶與思念,細膩地傳達彼此的情感。
所有人一同看著過往的相簿,生者追憶過往的人,過往的人看著自己的喪禮。
縱使先前有過多少別離,在生命的底端,彷彿再怎麼不完滿終究都會成為一種完滿。
面對人生的終局時,人總是對那股未知感到不安。
同時又交雜了那極其複雜的情感─恐懼、對人世的眷戀、終於能與思年多年的亡者共聚的那股欣喜。
波米叔叔說,這就好像他以前上台報告時的那種感受,他常常緊張地吃不下飯,但奇怪地又帶著一點興奮。
波米叔叔緊擁著亡妻的鬼魂,傾訴自己內心的脆弱,也是本片中最動人的生命盡頭的寫照。
在最後的那幾天,波米叔叔沒做什麼特別的大事,只是靜靜地過著那悠然的日子。
在微風的輕拂下,透著陽光的樹蔭下,睡著午覺。
一股即將離開人世的預感,帶領所有人越過野嶺深山,走進生命的源頭,在那裡與自己的前世或好幾代前自己的靈魂相遇。
所有人靜觀一個生命的消逝,就像在一個黑暗的洞穴中,慢慢發現岩壁上的礦石閃閃發光如同夜空中的銀河一般。
Apichatphong以攝影機書寫一首獻給生死的田園詩。
詩中一切平靜如水,就好像生命是一條長流的細水。
時光靜謐地在光影間流轉。
如果海明威的巴黎是席流動的饗宴,那麼波米叔叔的最後一程也就是一場越過生死訴說生命的流動的饗宴。
8 ) 《和急切说拜拜》
我这段时间几乎和不急不躁的电影们来了一次又一次的心灵接触,它们让我不断感觉到“不急切”的有效性和重要性。
这对于每一个人来说,是绝对有启迪作用的。
急切带来快速的同时,也带来了过耗、毛躁和轻浮。
虽然我并不觉得轻浮有何不可,但节奏总是忽快忽慢才有意思。
一味的快和一味的慢都并非具有节奏感。
阿彼察邦的电影便没有节奏,但剪辑帮助了它。
“有一种宁静叫庄严”,这句话极其适用于《能召回前世的布米叔叔》。
布米叔叔在夏夜和关心自己的人慢慢品尝菜肴时,死去的妻子鬼魂和失踪多年的儿子均一一出现。
这幕场景可爱而恬淡,布米叔叔忍着肾痛躺在农场中的小卧榻时,我耳边还回响着他对于蜂蜜的赞美——“它们吃起来很有嚼头”。
《能召回前世的布米叔叔》嚼头很持久,它始终笼罩在雾气蒙蒙的神秘里。
泰国的鬼神文化在影片中丝丝入扣,它们远不及南亚恐怖电影里“降头”、“邪神”恐怖,反而让人觉得清新和自然,带着浓浓的土腥味儿。
阿彼察邦只在影片结尾稍稍露出了一丝幽暗气息,但很快又被他自己通过密度更高的氤氲遮掩。
这个似乎是同性恋的导演就像是从不会流汗的青蛙,身处潮湿炎热的热带雨林中。
当有快跑而过的生灵经过时,它只是闪动一下眼睛,然后继续盈盈地呼吸。
2012年5月8日
9 ) 阿彼察邦·韦拉斯哈古风格笔记
作者:csh在英国在线电影杂志《电子羊》(Electric Sheep)的一篇访谈中,当阿彼察邦被问及自己电影的开放性意义时,他答道;“这很有趣,因为这意味着电影拥有了自己的生命。
”[1]阿彼察邦的作品那种迷人的多义性,总是让我们感到手忙脚乱。
当我们阐释其中的政治指涉时,我们可能会忽略它的自然主义意味;当我们用使用所谓的“东方美学”进行概括时,我们可能就忽略了那些具有跨文化普遍性的内涵。
因此,对于阿彼察邦风格的概述,就成为了非常重要的前提。
首先,以风格分析为基础,可以防止我们落入概念先行的窠臼。
其次,电影的叙事性、情绪性、象征性意义,都是需要通过视听风格来传达的。
在好莱坞商业电影中,正是继承自古典主义时代的连贯性风格(正反打、视线匹配等),清晰而流畅地完成了叙事目的。
而在阿彼察邦的多义性影像中,无论是哪一种意义,都是由他的电影语言系统所传达的。
最后,对于这样一位以创新性的电影形式闻名世界的导演来说,思考他“怎么说”,可能要比“说了什么”更为重要。
一、 场面调度在我们讨论阿彼察邦的独特性之前,首先要厘清他与所处传统的契合之处。
正如阿彼察邦在访谈中所提及的那样,他的创作深受台湾导演蔡明亮的影响[2]。
从阿彼察邦与蔡明亮的共通之处中,我们可以看到亚洲电影的一种区域性传统,这种传统被电影史学家大卫·波德维尔称为“亚洲极简主义”。
以侯孝贤、蔡明亮为代表的台湾新浪潮导演,是这种“极简主义”风格的先驱者。
这种风格强调固定机位长镜头的使用,景别也通常以中远景为主。
它非常适用于松散的情节,也让导演能够通过独特的场面调度,让我们更好地关注画面中的细节[3]。
阿彼察邦之所以被许多人定义为“长镜头导演”,恰恰就是由于他对于这种区域性传统的继承。
在他的作品里,我们常常可以看到这种中远景机位的固定镜头,以及包含多名角色的场面调度。
但是,不同的导演会将这种风格用于不同的目的,阿彼察邦在讲述他那似真若幻、夹杂着隐喻与传说的故事时,也会对这种传统进行调整与发展。
都是运用中远景固定长镜头内的场面调度,侯孝贤让我们看到了纷繁复杂的群像互动,蔡明亮用惊人的镜头长度让我们关注那些极细微的动作,北野武展现了冷幽默与触目惊心的暴力,洪常秀则把玩着人际关系中细腻的情绪变化——同样地,阿彼察邦当然也有自己擅长的东西。
1、 散点调度在好莱坞的古典主义电影中,导演们为了让我们持续性地关注明星、主角以及少数最为重要的信息,会让这些元素长久地处于画面中心、让特定角色面对着我们,或是采用偏向性较强的打光。
如果将这种策略称为“定点调度”的话,那么阿彼察邦的调度就可以被称为“散点调度”。
在阿彼察邦运用调度的时候,他会使用相对松散、灵活的构图,而且,几乎不会有哪个角色,会在中远景画面中总处于支配性地位。
叙事层面的主角,常常会在构图中扮演旁观者的角色(片例:《热带疾病》24:26-24:38;《幻梦墓园》[Cemetery of Splendour, 2015]112:46-113:42);在进入下一个画面的时候,常常需要进行一番等待,我们熟悉的主角才会入场,他们甚至还可能消隐在人群之中(片例:《幻梦墓园》74:25-75:13);此外,画面中的重心也不是恒定不变的,它们会随着镜头的进展,不断地发生变化(片例:《正午显影》37:02-41:34)。
最令人难忘的一个场景,或许是《能召回前世的布米叔叔》中的那场鬼魂显灵戏(15:46-17:23)。
在这个将近两分钟的远景长镜头中,构图起初处于一种失衡的状态。
影片的主角布米叔叔位于右侧角落的暗影处(此前提到过的旁观者手法),其余的两个角色也全部处于画面的右侧。
在空荡荡的左侧空间中,那张空着的椅子,却享受着明亮的打光。
这让观众体认到一种不安与期待感,但出乎我们意料的是,我们看到的不是一个“人”的入场,而是一位隐隐浮现的亡灵。
通过这种散点调度,阿彼察邦呈现了一种涵盖众多人物(乃至鬼魂)的日常状态,而不是那种以特定角色为中心的故事。
此外,这种手法还能让观众更关注人物周围的环境与景观。
2、 多重画框与自然环境在中远景的固定长镜头中,门扉、窗框等几何形体构成的画内画框,就可以成为非常重要的指示性元素。
沟口健二、侯孝贤、阿尔弗雷德·希区柯克都是使用这种技巧的大师。
在阿彼察邦的作品中,这种多重画框也可以成为散点调度的一部分。
在此前讨论过的那场《热带疾病》的戏(24:26-24:38)中,影片里的两位主角正在一旁观看兽医的手术。
医护人员们就处于一个窗框构成的画内画框中,这种强调性的构图,让两位主角在这个画面中的存在感变得更为微弱。
但是,阿彼察邦的独特之处在于,他擅长利用自然物体构成的画内画框进行叙事。
在《祝福》里,我们看到大量利用树木或植株创造画内画框的镜头(85:55-88:48);在《能召回前世的布米叔叔》中,那些利用峡谷和山岩构成画内画框的镜头,令人印象深刻(73:58-77:36)。
这种手法既丰富了画内画框的表现形态,也赋予了自然环境某种生命力。
3、 背面视角人类的面部表情,通常是一幅画面中最为引人注目的元素。
在当代大多数的主流电影中,近景和特写成为了最具存在感的两种景别,由此,对于面部表情的控制,也成为了当代电影表演艺术的重要组成部分。
但在这样的风格环境下,阿彼察邦似乎对背面视角情有独钟。
让镜头从背面审视人物——意大利导演安东尼奥尼是系统地使用这种手法的先驱者,他由此创造了一种缄默的、去戏剧化的效果,并使之成为了现代主义电影的代表技巧之一。
在让-马里·斯特劳布夫妇的作品中,可以看到对这种技巧的极端使用。
这种手法一方面促使我们去揣测角色的心理状态,另一方面引导我们去关注人物周围的环境。
与多重画框一样,阿彼察邦对于背面视角的使用,也可以看作是散点调度的组成部分之一。
安东尼奥尼偏爱45°倾角,斯特劳布夫妇倾向于让角色直接背对摄影机,而阿彼察邦的角色,是以相对闲散的姿态背对观众的。
他的角色背对摄影机的角度各不相同,而且会随着场景的进展,他会适时地运用剪辑突出重点,或是让人物露出更多的侧脸(片例:《祝福》37:43-39:10;《幻梦墓园》81:47-83:27)。
这让他在抑制情绪、强调环境的同时,也创造出一种日常化的状态——我们的生活不等于那些正面大特写,但也同样不等于那些现代主义的艰涩影像。
二、 运动镜头与剪辑很多人会把阿彼察邦简单地定义为一个“固定长镜头”导演,确实,他的影片基本上是由运动幅度不大的长镜头构成的。
但是,如果深究他的作品会发现,他的影像要比大多数人想象的更具包容性。
他拥有一套“组合式”的视听语言系统——他会使用中远景固定镜头内的调度,但他不会像大多数蔡明亮或洪常秀的作品那样,放弃剪辑、运动镜头乃至手持镜头的力量,他甚至会使用正反打的变体……但是,他会调整、发展这些相对次要的技巧,使之强化主要技巧的功能。
1、 交通工具与运动镜头关于阿彼察邦对于交通工具的偏爱,在国内已经有相关的著述[4]。
他自己也在访谈中表示,“我钟爱那种梦幻、流动、自由的形式……对我来说,电影院和汽车是一样的,它们都会将观众传送到未知的地方。
”[5]如果说固定镜头内的散点调度,让阿彼察邦得以呈现某种情境,那么运动镜头就是他在不同的情境之间进行传送的通道。
阿彼察邦会用固定镜头来表现交通工具内部的场景,同时用运动镜头来呈现车外的景观。
有趣的是,在这样的时刻,他很少使用多重画框(很多导演会用车窗内部飞逝的风景,来展现交通工具的存在),他会使用纯粹的、运动着的风景(片例:《祝福》24:42-26:15;《恋爱症候群》32:40-32:54)。
这种镜头会创造一种很有趣的效果,它们就如同交通工具的“视点镜头”——《祝福》的那个镜头,显然不是两位车内角色的视点镜头,因为这个镜头是向“后”看的。
正因如此,这种镜头不仅能够让观众们纯粹地关注画面中的景观,也为这种运载过程赋予了某种灵性。
2、 手持镜头在阿彼察邦的影片里,这种传送通道,并不仅仅是那些与交通工具相关联的、稳定的运动镜头。
当他的角色亲自闯入一个不同的环境时,不稳定的手持镜头便登场了。
在《能召回前世的布米叔叔》中,当布米叔叔在丛林中穿梭时,颤动的手持镜头呼应着他的喘气声(72:42-73:53);在《恋爱症候群》中,当两位医生走入地下室的时候,我们也看到了一个明暗交替的手持长镜头(68:07-69:08)。
上述这两部作品,均包含了大量的固定机位长镜头。
这些景别相对逼仄的手持镜头,就显得格外突出。
正如观众经由电影,被传送到未知之地一样,这些影片中的角色,也从一种稳定的情境,从风格层面上被传送到另一种情境。
无论是布米叔叔还是那两位医生,都从相对稳定的现实出发,前往某种超自然的领域。
3、 正反打变体在好莱坞的古典主义连贯性风格中,正反打是最为重要的技巧之一。
它可以让我们在恰当的时候,观察对话双方中更重要的角色。
正反打又名“过肩正反打”,这是因为在A听B说话的时候,我们常常会看到A模糊的肩部,这样我们就能同时体认谈话的双方。
在阿彼察邦的影片中,他也使用了这种技巧,但他却进行了幅度极大的调整。
在《恋爱症候群》的一场对话戏(52:10-52:42)中,对话双方都是直面镜头的——这是小津安二郎常常使用的技巧,而阿彼察邦的不同之处在于,他会延宕我们看到其中一位对话角色的时间(在此之前,他甚至让我们看到了对话双方之外的第三者)。
虽然我们可以听到那位男性角色的声音,但我们是在这场戏的晚期阶段才看到他的。
在《能召回前世的布米叔叔》的一场戏中(23:32-24:05),他还使用了另一种反打镜头的变体。
他让听话人与发言者占据画面中同等重要的位置,“过肩反打镜头”甚至成为了“过头反打镜头”。
无论是上述哪一种变体,都让我们更为强烈地意识到“听话人”的存在,让我们去揣测其表情乃至情绪。
从这个角度来说,这些变体的作用,其实与此前提到的背面视角十分相似。
三、总结根据上述的分析可以发现,我们不能用“长镜头导演”或“东方美学”,简单地概括阿彼察邦的风格特征。
确实,从他的影像中,我们可以找到沟口健二、小津安二郎、安东尼奥尼、侯孝贤乃至蔡明亮也曾用过的技巧。
在如今这个时代,大多数的基本技巧,都已经有了大师级的先例,而阿彼察邦的作品让我们看到,一位新生代的导演,如何能够通过微调、改造与融合,创造出属于自己的自己的风格系统。
总体而言,阿彼察邦·韦拉斯哈古的电影风格,是以中远景固定镜头内的场面调度为基础的,他采用了相对灵活的构图模式、结合自然环境的多重画框,以及多样化的背面视角。
这种闲散、灵动的影像,可以创造一种日常化的情境、传达相对含蓄的情绪,也会引导观众更关注人物周围的环境。
在这个基础之外,他也并不排斥运动镜头、手持镜头与剪辑的使用,但这些次要元素的功能,也服务于上述的——例如,运动镜头成为了联结两种情境的桥梁,“过头反打”也创造了背面视角的效果。
[1] http://www.electricsheepmagazine.co.uk/2009/12/01/interview-with-apichatpong-weerasethakul/[2] http://ent.163.com/10/0523/07/67BQV4ML00034D8N.html[3] David Bordwell, “Beyond Asian Minimalism: Hong Sangsoo's Geometry Lesson,” in Korean Film Directors Series: Hong Sang-soo, ed. Huh Moonyung (Seoul: Korean Film Council, 2007), 19-30.[4] 《流动的空间——阿彼察邦电影中交通工具的美学分析》,《电影评介》,2018年第17期,第80-83页。
[5] Holger Romers, “Creating His Own Cinematic Language: An Interview with Apichatpong Weerasethakul”, in Cineaste, 2005, fall.
10 ) 没有叙事包袱
这又是一部很淡的电影,淡到你会逐渐放弃对情节和戏剧冲突的期待。
但就在你毫无准备的时候,鬼魂出现了,过一会,猴灵(野人)又出现了,克服了短暂的不适之后,一家人(人、鬼、野人)又围坐在桌边继续聊天。
这种反常中的日常是本片给我的第一个惊喜。
鬼的形象在中国电影中也经常出现,但它永远是以一个令人恐怖的客体出现的,我们永远不能摆脱来自它的那种凝视。
无论它以什么面目出现,我们都知道背后潜藏着一个恐怖的真实面目。
比如画皮,在娇艳如花的美女面孔下有一张鬼脸;而小倩,纵然她无害人之心,但她背后依然有一个邪恶的黑山老妖,在这里,小倩只不过是鬼的人格化包装,它掩盖不了鬼作为恐怖客体的事实。
人、鬼的二元对立是中国鬼片的基本叙事伦理。
但在此片中,鬼和野人不具备这种恐怖的凝视,或者说具体到这二“人”身上,这种恐惧被亲情遮蔽了,鬼和野人在这只是人的另一种平等的形态,他们都被包括在家庭这个共同体内。
鬼和野人并不是推动情节发展的关键,他们只是作为角色出现。
第二处高潮出现在那个盛装女人在水中和鲶鱼做爱时。
这是个自我献祭的意象,充满了宗教意味。
鲶鱼在这充当了那个阳物能指,一个纯粹的,独立于男性身体之外的阳物。
这种想象非常东方,这是东方主义的生殖崇拜,可以把崇拜对象具体到阳物本身,而不再需要一个人格化的男神。
第三处高潮出现在一行人进入溶洞时,这一段主动镜头非常精彩。
溶洞作为子宫的隐喻,成为波米叔叔回溯人生的最后场景,这里甚至插入了一段关于军队的回忆。
原以为会对这段政治指涉进行发展,没想到也是一笔带过,就像其他的方面一样。
结尾也算是个小高潮,灵魂出窍的镜头很有想象力。
这部片子的叙事不太有逻辑,基本上就是几个章节的拼贴。
或者说,导演刻意弱化了情节性,让我们能摆脱叙事包袱,而把注意力转移到导演所营造的东南亚独特的文化气氛上。
叙事的结果不是目的,过程才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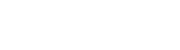




















让人想起是枝裕和的《下一站天国》,然而平实化的制作中似乎又不甘心地掺杂了一些影像的政治……
看的我闷得慌~~无聊死了~
前身,今生,來世;獸,人,鬼。
其实没怎么看懂。改天再看一遍……
除却宗教性质的顿悟,我想阿彼察邦的心理年龄一定超过50岁,才能用如此平静的镜头和晦涩的隐喻来分析自我,解剖人生。热带乡村的景色, 让我想起南方的童年夏天。很喜欢水牛和洞穴那两段,只是猴子的造型太像B级片廉价造型;最后的镜像有点像浮世绘风格的MV
影片旨在探讨宿命轮回的艰深命题,灵魂安歇与生命赎罪,都安置在了一片广袤的热带雨林和一窟隐秘的洞穴之中。导演在刻意标榜自己的风格,但这种风格的纪实,也更像是在顺应一种粗砺的影像质感,从而也平缓叙述清楚了导演中意的自然法则的力量。泰国有本土性的宗教色彩,所以其影片的神学性也很浓厚。
假设它真的是部好电影,三星已是极限。内容、形式都极单薄,靠着这种极单薄所支撑起的虚无与神秘主义,本身就意味着幌子。
想拥有鬼猴同款cosplay服。
阿彼察邦是想用这些看不懂的符号来取悦对东方文化有兴趣但其实又只是赶个时髦一知半解的评委么?这金棕榈真是碰上了伯顿的奇情口味。
……这,这,这……
幽暗、神秘、寂静、缓慢,东南亚热带丛林里的奇妙故事,梦境与现实只有一线之隔,凡人与鬼怪的平等对话,抽离的灵魂和呆坐的身体究竟哪一个才更真实。“天堂并没有想象中的好,那里什么都没有。”摄影和打光非常厉害,几度惊叹这光到底怎么打的。。
实在。。。想给两星。。。。
Facing the jungle, the hills and vales, my past lives as an animal and other beings rise up before me.我望着山林溪谷前世化作动物与众生跃然眼前第四部阿彼察邦,也是最混沌精怪,最考验耐性的一部。从小接触的民俗怪谈、东方生死观让你不得不与之产生亲切的共鸣,奇妙的感觉皆在观影结束的那一刹那才涌现出来(最后再看记忆!)
多次元纵向空间,真梦(直接切换,不容易察觉,没有采用叠化等方式)、真人、假身(肉身、动物)三重存在。《热带疾病》最优,《布米叔叔》值得欣赏。
看了影评后才明白一点点,不适合外国人看的片子啊风景和光的运用还是满迷人的
PS:前半段桌前家人阴阳聚会的场景让我穿越到雷乃《几度春风几度霜》,而后半段顿觉颇像大岛渚《被迫情死的日本之夏》。总之,2013第一部10星片就给你了。
安静缓慢又美丽,还猎奇。
十九年了,阿珍,你還是四十二歲,可我的手已經蒼老。如同當年看光明的未來,看到結尾,心動彈不得,一股比欲哭無淚更強大的空虛撲面而來。
奇妙的一塌糊涂。其实故事内核如果抛开公主一段,则极其简单,一个将瞎且将死之人所看到和所想的人生。但是换成影像,则极端的迷人,摄影很好看,录音让人彷佛置于泰国的农村。更难以讲述的是,对土地和对母体的眷念,全凭自己感悟了。最后似乎从乡村离开,布米叔叔最终死去。
(2014年春重估)如今的我完全适应阿彼察邦了,因缘际会,历经死生便可同游太虚啊,还是觉得略矫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