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希望的另一面》剧情介绍
一个叫做哈立德的年轻叙利亚难民几乎失去了所有的家人。近乎偶然之下,他藏在一艘运煤船里流落到赫尔辛基成了一个偷渡客,并在当地寻求政治庇护。维克斯特伦是一个旅行推销员,他在牌桌上赢了一大笔钱之后在赫尔辛基的一条后街买了一家不赚钱的餐馆。在当地政府作出要将哈立德遣返回阿勒颇的判决后,他决定非法留在这个国家。最终,维克斯特伦发现哈立德睡在他餐馆的内院里,并聘请他到自己餐馆里做清洁工和洗碗工。生活会短暂地向我们展示它光明的一面,然而命运很快就会插手其中。热播电视剧最新电影斯亚码勇士花生酱三明治夜莺之旅老有所依生存家族格列佛最后的旅行闺怨晴空战士以吻之名小塔历险记之记忆森林食女忍无可忍萨贝尔还很年轻人生不再重来创:战纪黑蝴蝶难以置信的爱让爱传出去跳过的青春姐姐的小狼友我是业主五个相扑的少年恐怖快递半透明水谜之忽然奢华艾玛酒国之王滹沱儿女英村脑残故事第二季亨利小上帝大写的印刷体
《希望的另一面》长篇影评
1 ) 或许人生不是赛道
北京电影节观看的,总体来讲,影片给四星,立意满分,音乐满分,配色灯光满分,但叙事、剪辑和演员的表现力都有相应的欠缺。
我想根据其立意,简单聊聊。
当一个孩子出生,TA降临的国家、城市、家庭的环境、秩序与模样,对其的一生起着百分百的影响。
用我自身做个简单的对比。
影片中的哈立德在家乡叙利亚目睹房屋被炸、亲人遇难,与世间仅剩的亲人妹妹向欧洲逃难,祈求申请庇护。
中途与妹妹走散,他唯一的动力就是找到妹妹,与妹妹在芬兰生活下去。
这个“生活”的要求,就是有地儿睡觉,有饭吃,不受欺凌。
而我出生在和平的年代与国度,家人安好,吃穿住不愁,目前生活的动力是努力实现个人价值(其实可能只是追求名利)。
以前我总爱拿自己和富二代、官二代、学二代对比,总有“觉得自己输在了起跑线”等想法,进而引申到社会阶级分化等思考。
可当我和哈立德对比,自己已经足够幸运、幸福。
我能说哈立德是不幸的吗?
显然不能,他经历了巨大的身心痛苦,付出我这个中国小康家庭的孩子难以想象的艰辛努力,终于找到了唯一的亲人,有了落脚地。
片尾他终于露出的微笑,观众都能体会到他满满的幸福感。
再说回到我自己身上。
以前我认为人生是条直线赛道,有人幸运生在了终点,有人倒霉输在了起跑线。
现在意识这种想法是不对的。
若要重新比喻,那现在我认为,人生是个圆圈。
起点可能是终点,终点也许是起点。
不在于互相追逐,在自己的圆圈上多经历多体验是种圆满,累了就停下也无妨。
可能最好的状态还是那句话:有所爱,有所期待。
根据今天的观影体验,再加一句:常感恩。
2 ) Honest man
个人记录,短评写不下。
1’Halid从船上下来的时候看了一眼船员,但是不知道什么感情。
后来在审判会的时候说,“一个好心的船员发现了我,没有告诉船长”。
后置。
先给一个果,再给因,不显得煽情,反而因为当时的误解,会有迟到的感动。
属于叙事的技巧,讲故事不动声色,高级。
2‘ 现实感来自于不做美化的直接呈现。
香烟烫进戒指,全是烟头的盘子,Halid 洗澡时的黑水,接待中心里人黑着眼眶无望的等待。
是的。
人生一些日子就是这样的。
一般对戏剧性似乎是为了挽救现实的平淡。
那是人们还不会看。
3’ 开场惊人。
丈夫走时复杂的愤怒与仇恨,妻子把戒指扔进烟灰缸,且直接把烟头扔进去。
结尾开了一家杂货铺,为转变提供点可信度。
4’ 歌曲一直提到 妈妈 我要死了 给我买件白衬衫吧 这么顺利、积极 只是为了对抗死亡 ‘我装作开心。
你应该如此,有用‘ 5’ Halid 在梳妆台梳头。
体面,尊严。
最后妹妹没有黑下去,她没丧失希望。
最感人可能是halid 坚持和妹妹在一起,确信只要两人在一起,所有生活都可以自己创造,而不依靠黑在芬兰,有个好老板。
但这个角色呈现有些复杂,说爱上芬兰又想离开,以及告诉妹妹黑身份可以给她一个全新的生活(说明他认可这种生活)但结局又随时准备好走,没想清楚。
6‘ 尊严还体现在老板,一点一点展现他的行为。
买衣服、卖衣服、先卖几件,然后卖掉整个库存,和食品店老板极为自信地要价格,经历行情不好。
带妹妹回来,被检查。
人不屈不挠。
不加修饰地展现人的行为,来体现人的尊严,继承自海明威,近了拉美Alonso 的 《自由》也是同理。
不写了。
3 ) 不要难过,人生总是有好有坏
歌很好听,轻快里带点沧桑,芬兰人们显然也很喜欢,可跳舞的时候依旧面无表情。
有始有终的面瘫和情景剧似的干脆的镜头切换,让这部电影呈现出略显怪异但非常有趣的气氛。
全片最神秘的人物大概是“好心人”,好心人无处不在,总能适时出场带领主角柳暗花明。
然而导演并不是一个天真乐观的理想主义者。
不然,在主角客观克制地讲述了自己的难民逃亡经历并不卑不亢地夸了芬兰一番后,庇护申请总该通过吧?
更何况,他在片尾还被捅了一刀呢。
担心观众因温情的剧情而弱化了难民问题的严重性,我觉得没什么必要。
指望“好心人帮助”这样的小概率事件度过难关,而非稳定健全的难民保护机制,这听起来不是很妙。
Too good to be true的情节设置,反而让人觉得有点丧丧的。
那些理想化的“天无绝人之路”,更像一个看透世事者的自我安慰:倒霉时别太难过,想要生活过得去,总是有好也有坏。
不过幽默的人总不会过得太糟——当然,芬兰人开玩笑的时候也是面瘫。
寿司那段恐怕没人不喜欢,恨不得扑进屏幕拯救无辜的芥末;被咸鱼寿司荼毒的客人们离开餐厅,失败的老板让员工回家,自己孤独地坐在店里,一旁的点歌机(?
)啪的一声灭了,真是惨淡哈哈哈。
很多好玩的小细节,导演镜头里面冷心热的芬兰人太可爱了。
4 ) 20180110个人观影感受
就像是平淡地叙述,每个人的脸上几乎都没有什么表情,甚至可以说麻木。
没有过多的情感去描述无奈,但却让人始终感觉压抑无奈,耗时一天才勉强看完。
办假证时得知主角大叔是91年的,90后大龄青年表示相当不淡定。
一直不太了解纳粹主义对亚裔的仇恨,在个人的印象中,犹太民族是勤奋聪明、努力生活的优秀民族,没想到现在还有新纳粹主义,觉得他们除了给社会造成不稳定似乎一无是处。
叙利亚的难民迁移,之前在新闻里就很关注,其实这是一件很无奈的事情,因为双方都将过得不好,并不是每一个难民都会像主角大叔一样感激,有的人也会因此而偏激地去伤害当地居民,更何况还有宗教信仰的巨大差异。
结尾主角大叔的满足微笑让人心酸,希望的另一面,还是需要自己本身去竭尽全力的努力。
5 ) 确有无缘之善,亦有无由之恶
我这么丧的人,大概就适合在这种披着惨淡外皮的电影里,遭遇突然降临的一段黑色幽默,然后自己一个人偷偷笑很久;然后走出放映厅,找到那首喜欢的不行的BGM,感到浅浅一股回流的心酸。
阿基的色彩太好看了!
海报完全无法体现这种美,所以换了一张剧照图。
也是电影里两股支线的直接交汇(第一次一脸煤灰的难民和驾车而过的离异男子不算的话)。
北欧中产阶级的人生问题,是轻描淡写了的,妻子酗酒+事业瓶颈(“市场不好了”一句都是通过旁人之口),再加上赌场之夜爆棚运气,和寿司之夜的荒诞喜剧,你根本不觉得他的人生有多大问题。
他好像永远都思路清晰,什么都能解决,可你看,他是极少极少带笑容的。
叙利亚难民的生存之苦,丧亲,分离,背井离乡,无名恶意。
是一个几乎没有私欲期待的人,每一步却和自己所期待的都背道而驰。
他问,假装快乐对我也有用吗?
——是很苦了,却没有卖苦。
回应的方式,是尽力陈述,是信仰尽头,是翻墙而逃,是一个拳头。
两个人的命运相逢,他给他带来了“新生活”,他给他解开了“旧仇怨”。
行动、果然是解开人的困顿的小诀窍啊。
讽刺不是没有。
政府一本正经的拒书之后,是电视报道里的现实。
没有刻意用镜头去逼近血腥,最严重也不过仓库里几滴浓稠的血液。
如果说命运的残酷是基底的话,阿基的暖却是通过旁人一点点小举措露出来的。
印象最深刻,是收容所面瘫护士临行前开门的动作,就好像两个废柴员工用身体挡住狗狗的身影一样——生而为人的、力所能及的善意。
恶呢,竟然也是没有来由。
有整体氛围的左,纳粹风味的右(“该死的犹太人”)也莫名“锲而不舍”了起来。
还是有点遗憾的。
阿基像所有柔软和温和的好人一样,有太多的“想当然”,所有的戏剧冲突都都被磨钝了些,最后河边等死戏,都感觉充满希望——大有一种空中童话的虚。
作为故事来看是好的,但题材和现实隔离太远,总觉得会留下艺术的隐患。
但还是很高兴我的“欧盟电影展”第一片是阿基。
八分给你。
❤️
6 ) 考里斯马基的奥斯维辛之路
在《希望的另一面》中,有一个文本性很强、颇值得玩味的段落:当主角阿里面对警员(同时面对镜头),将自己的逃亡经历娓娓道来时,看电影的我们和听故事的女警员形成有趣的呼应:两者同为叙述的受众,在一定距离外审视着故事,并在心中作出自己的评价。
从这个角度看,导演阿基·考里斯马基似乎抛弃了摄影机的“纪录”属性,若有若无地出现在影像与观众的中间,而摄影机化身成类似小说中“叙述者”的角色,从而使电影散发出迷人的文学意味。
可以说,即使不看影片的政治色彩,阿基的发挥也无愧于这座银熊了。
《希望的另一面》是一个与难民有关的故事,而难民问题已成为近几年各大电影节的热门话题。
然而,处理电影艺术与政治主题的关系一直是令创作者感到棘手的难题。
阿多诺曾说“奥斯维辛之后,写诗是残忍的”。
他实际上对一切艺术形式,尤其是电影,提出了一种战后语境下的质疑。
这里的困难在于,一方面,影像的真实时空属性使电影拥有了前所未有的感召力与宣传力,从而令一切现实主义都可能沦为政治的传声筒;可另一方面,背叛真实便是背叛电影本身。
那么,电影如何通向奥斯维辛?
至少在戈达尔眼中,战后的意大利人和法国人都在“通向奥斯维辛”的道路上作出了自己的努力:他的《电影史》阐释的就是这段历史。
而如今,接力棒交到了阿基的手上,他就像一位集大成者(当然,他自谦地说这只是“借鉴融合”),借用前人的衣钵生成了自己的风格:冷幽默又不失温情,优雅却直击现实。
“阿基氏冷幽默”体现在演员调度上。
特写镜头中演员时常出现的木然表情与近景镜头中略显僵硬的肢体动作“相得益彰”,这种“拙劣”的表演往往造成零点几秒尴尬的沉默。
这尴尬恰恰是幽默感的源头,使人不得不想起雅克·塔蒂和他的于洛先生,而这种“无表演”的表演又隐秘地联系到了布列松甚至是小津对演员的调度。
在这里,当演员成为模特甚至容器时,他们的表演宣示了影片的寓言属性和一个潜在的叙述者,而影像也因此具有了文学属性,映射其所指。
我们能强烈地感受到阿基眼中的芬兰人民和欧洲难民的“众生相”,也感受到他对政府道义责任的追问,对难民群体的同情与尊重,以及对芬兰大众高尚人格的敬意与信心。
而通过上述表演上的风格化处理,阿基既成功地绕开了《我是布莱克》所遭遇的关于人物脱离叙事链条后其普遍性是否成立的质疑,又避免了类似《山河故人》一样追求宏大叙事导致人物扁平化的困境。
总之,阿基用它的风格化作为“护身符”,成功地回应了阿多诺的诘问。
值得说明的是,阿基镜头下的演员继承了布列松的疏离感,却无意于继承其冷漠感。
相对于布列松对演员表演的“压缩”,《希望的另一面》中演员的动作笨拙却清楚地展现目的,仿佛是厌倦于语言交流时的虚伪和迂回,才选择用动作“直抒胸臆”。
在这样的调度下,人物也被带上了淳朴、坦诚、善良的性格特点,连“抽提成”这种不太光彩的举动也透出一股憨厚。
至此,阿基的演员们终于完成了其使命:通过(无)表演展现人物个性,并以自身为载体,将这些元素通过寓言式的指代,投射到整个族群。
事实上,这种风格化的处理方式在影片中前后呼应,处处可见:影片中餐厅、酒吧、音乐等元素的重复出现,单调“无聊”的特写与近景镜头等,这一切无不体现了导演的坦诚与克制。
其坦诚在于用极简的形式来“暴露虚假”,而其克制在于通过暴露虚假来创造间离感,推开观众,远离廉价的煽情。
可以说对于“难民问题”这种大热题材,这种距离是优雅且必要的,而这种运用镜头进行的“书写”活动,也让阿基的虚构获得了现实关怀——观众对故事的真假并不拘泥,且会认为这是对社会的一种“真实”写照。
真实在“虚假”的基础上,得以在电影中重构。
然而,当我提到导演“似乎抛弃了摄影机的纪录属性”时,需要强调的是,阿基绝非“背叛了电影本身”,而影片的另一大魅力所在,恰恰是其在“暴露虚假”的同时,精心地保留住影像的现实特质, 将这个“寓言故事”从空洞扁平的“符号化”陷阱中拉了回来。
在《希望的另一面》中,阿基巧妙地做了与德·西卡相似的处理:他小心翼翼地“安排”情节,让事件间的起承转合绕开戏剧化的因果律,并加入大量诸如去酒吧听歌、将餐馆改作日料店的“闲笔”。
当我们沉醉在北欧味十足的轻摇滚旋律中时,影像亦得以保持真实事件全部的“具体性,独特性和事实的含糊性”,其力量也得到了充分发挥。
这种自然的、随着时间流逝而“偶然地”观察事件的美学无疑来自新现实主义的遗泽,而阿基在此基础上,可以说是推陈出新,更近一步。
如果说《偷自行车的人》用影像“观察”到了某种现实,那么在《希望的另一面》中,阿基则是漂亮地将“观察到的现实”进行风格化的处理,并在此基础上“重构”了一层指代意义上的现实。
这种用“真实重构真实”的风格化处理无疑获得了丰富的美学效果,即作为一个左翼艺术家,对政治进行批评与讽刺的同时,也作为一个敏感的艺术创作者,用影像凸显出人性的高尚和希望的光辉。
原载http://www.sohu.com/a/200672325_176400,有删改
7 ) 当欧洲难民遇到尴尬癌民族
2015年,欧洲爆发难民危机,仅仅一年,欧洲的新增非法移民就达到150万,超过前几年总和。
近百万来自中东,非洲的难民背井离乡,在异国的欧洲大陆等待避难申请被批准。
他们生活困窘,而等待着他们的是寒冬一样的未来。
难民潮的涌入给欧洲各国带来沉重的经济与社会压力,在欧盟内部造成了巨大的分歧。
欧洲各国在国情与人道之间左右摇摆,加上各地频发的袭击事件,合作进程屡屡中断。
原本开放包容的一体化格局陷入泥淖。
边境管制加强;原本欧洲人民开放的社会文化也逐渐变得排外,社区冲突不断。
难民潮虽在2017年明显回落,大量难民仍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
时至今日,席卷欧洲的难民潮,依旧是一个敏感又令人束手无策的话题。
世上大抵没有多少个导演会像芬兰怪杰 阿基·考里斯马基 一样,够胆拿难民潮来开玩笑。
影片就发生在如此紧张的难民危机背景下。
影片在谈笑中描绘了难民的苦涩遭遇,又带点超现实看淡世情的荒诞感,阿基在这部电影中把他的独门冷幽默挥洒得淋漓尽致。
影片讲述了叙利亚青年哈立德为了逃避战火偷渡到芬兰寻求政治庇护,一上岸就碰壁官僚制度遭遇遣返。
于是哈立德决定“我命由我不由天”逃出一片生天,流落街头期间撞见刚离开酗酒老婆买了间餐厅的落魄老板维克斯特伦。
两个同是天涯沦落人不打不相识,跌跌撞撞互相扶持希望重过新生的故事。
电影通篇明明讲述了一个悲伤沉重的难民故事,但当你看着片子的人物在生活的重压下苦中作乐时,偏偏禁不住发笑,又忍不住落泪。
在背景无处不透露的悲凉气氛和令人失望的人性中,似乎掺入了一丝曙光,正如影片的名字一样。
阿基用超凡脱俗的荒诞性,将一个悲伤的难民故事描绘成了一部人道主义喜剧。
故事吸收了难民潮的思想,以不可思议的轻松和简单拥抱了这个故事,却没有以任何方式破坏其严肃性。
比起单纯描绘难民悲惨的生活,这样诉说故事明显难度更高,感染力也更强。
对于那些从未看过阿基电影的人,这里有一个小指南:他曾评价自己为“世界上最好的电影制作人,但拍出来的电影最烂”。
阿基与传统的电影制作人相比而言非常与众不同,他重新定义了极简主义的概念。
他片中的主角通常是穷困潦倒,跌落谷底,备受压迫的人,然后在生活的角落找到某些小小的慰籍。
他的电影是极简的典范:没有表情,没有特效,没有追车,没有大嗓门,人物只是在屏幕上走来走去,面无表情,宠辱不惊,似乎只是个没得感情的机器罢了。
不仅如此,在他的电影中,似乎镜头的微微移动都是一种奢侈。
正是这种没有多余的画面,带来了一种看破红尘的智慧,一种对世界严酷的厌倦感。
片中的轻微的喜剧效果轻松却令人捉摸不透,或许每一位观众都在观影中对人物们的半冷漠感到困惑,却仍不可阻挡地坚持下去。
而影片的所在地芬兰,似乎给片中人们的“冷漠脸”贴上了一个情有可原的标签。
还记得之前火出圈的芬兰人的自闭属性吗?
片中的没得感情的机器人演绎与芬兰人天生自带的自闭属性简直完美契合。
在冷酷仙境的芬兰,人们为了不与陌生人接触,那可是使出了洪荒之力:公交站人流之间两米的距离;公园距离感十足的单人椅子……像是所有人的脑内都有一道“保持距离”的程序输入,芬兰人总是不约而同的选择与人隔开几米远,不少外国人也对芬兰人的这种内敛表示惊讶以及有趣。
看到这里,你可能就会想了,难民在芬兰不可能感受到温暖的吧!
然而看着看着,似乎你就明白了那种,在北极圈的极寒下,人们惺惺相惜,外冷内热的感情。
这部电影由两条主线组成:一位来自叙利亚的难民,在人生地不熟的芬兰请求庇护,却遭遇官僚制度的无奈;一位失去家庭的的中年男子,利用扑克豪赌的钱进军餐饮业,却大搞地狱料理把餐厅经营得一塌糊涂。
导演精心安排了这样荒谬可笑的两种人的经历,看上去似乎是两个独立故事。
然而,他们共同的凄凉遭遇让我们对两人有一种同病相怜的同情,这种轻盈的触感,让我们相信着两条平行线终有相交的一天。
不出所料地,当哈立德被移民局非常礼貌地拒绝后,他开始了潜逃。
流落街头时遇上出来倒垃圾的老板,争抢着垃圾桶的所属权,两个同是天涯沦落人不打不相识,跌跌撞撞过后意外互相扶持,希望活出新生。
安静的街角,蓝调的民谣抚慰着小人物寂寞的心,昏暗的垃圾场,冷面热心的人伸出援手,一起讪笑官僚无情。
维克斯特伦的餐厅看起来是一个糟糕的就餐场所,尤其是当老板决定将其改造成寿司店的时候——比鱼片还厚的芥末酱膏让离店的人络绎不绝。
但它对老板与哈立德而言仍然是一种乌托邦式的场所,是一个与外面对他们追啦喊打麻将格格不入的古怪共和国。
在这里的日常带给这两个落魄的人从未体验过的家的归属感。
这似乎应了一开始庇护所里的朋友马扎克的那句深刻而微妙的玩笑话:芬兰会驱逐忧郁的人,但也不要刻意开心。
芬兰是一个经历极夜寒冬,充满了疲倦与坚忍的国家。
来自芬兰的人经常会说冬天的芬兰很抑郁,他们躲在屋内暖炉后耷拉着脸,吃着平淡无奇的食物或是鳕鱼汤。
也许马扎克是对的,政府希望接纳乐观的移民,给他们带来必要的欢乐。
片末的哈立德,背负着遣返的悲伤,却找到了归宿,这样矛盾而平衡的人格,有为这样的芬兰带来一些特殊的色彩吧?
再回到本片的导演,与其说他是一个乐于运用黑色幽默的电影人,不如说他是一个用微笑讽刺国家弱点的观察者,一个在阴暗之中挖掘社会美好的坚定良知的人。
正如哈立德所经历的那样,赫尔辛基也有它的黑暗面:他受到过种族主义的攻击,也受到过官僚们的阻挠。
然而,他也在这样的环境中,遇到了普通芬兰人那种不多愁善感、甚至有点不情不愿的善良。
当他告诉马扎克,他爱上了自己的新家时,我们都能够理解为什么。
这并不是一部关于奋斗和坚强的天真故事,相反,它真实又巧妙。
正是这种在昏暗中对于人性美好的颂扬,使得希望在彼方出现。
8 ) 简单的力量
说实在的,我是第一次看阿基导演的电影,感觉很好。
因为是去年的新片,所以不抱什么太大的希望,时间是最好的观众,在若干年后浮出水面的好电影,才是真正的好电影,而这部恰恰不是,这真是让人意外的惊喜。
网上这个中文翻译并不太好,我看的题目翻译是《另一面的希望》其实这个说法会更加贴切主题,“另一面的希望”是比较阳光的,至少也是希望;而“希望的另一面”就不好说了,就显示不出这本影片的喜剧效果。
这本电影最好的就是对比特别到位,这样一个沉重的话题,让人们去直面它,导演的方法是排除一切杂乱的干扰,让它的本质浮现,然后加以反差对比,起到一个喜剧的效果。
主人翁在酒馆喝闷酒,门口艺人弹着一首好听的歌曲,这既是对比,又是主线的延伸与升华。
9 ) [Film Review] The Other Side of Hope (2017) and Fallen Leaves (2023)
Entering into the 21st century, Aki Kaurismäki’s prolific career slows down tolerably, only 5 features in 23 years, but it also marks a harvest season for a filmmaker of such a unique style and sentiment. THE OTHER SIDE OF HOPE nabs him Best Director in Berlin and FALLEN LEAVES is the recipient of Jury Prize in Cannes. Both films take place in Helsinki, the former is a bifurcating story about a young Syrian asylum seeker Khaled Ali (Sherwan Haji) and Waldemar Wikström (Kuosmanen), a middle-aged local career-changing restauranteur, both want to start their lives anew, but life is not fair, Wikström can scoop a sizable fortune overnight in a poker game whereas Ali’s heart-rending plea has zero chance to pass the bureaucratic flintiness. But their paths eventually are crossed, comedic episodes alternate with dramatic occurrences (the restaurant’s inutile attempt to wheel out Japanese cuisine is a total gas!), the big reunion of Ali and his sister Miriam (played by Sherwan’s own sister Niroz) pays off grandly without falling into a drippy trap, Ali trusts Miriam’s decision to apply for asylum seeker even though he knows from experience it is a tall order, and the ambivalent coda (with the racism and identitarian menace remains the bane for an immigrant) is marvelously touched up by a canine tenderness, which also crops up in FALLEN LEAVES. On the strength of Haji’s dignified, roundly relatable performance which uncloaks Ali’s smoldering frustration and trepidation, consolidates his resolute in regarding all the setbacks without blinking an eye, and Kuosmanen’s expertly conveyed compassion, Kaurismäki makes a compelling case appealing to our commiserations apropos of the immigrants crisis in Europe through Ali’s quandary and Wikström’s altruism.
FALLEN LEAVES is a romance, but with a difference, Ansa (Pöysti) and Holappa (Vatanen) are two working-class lonesome souls in their late 30s or early 40s. She is a zero-hour contract employee in a supermarket and he is a sandblaster, neither manages to keep it for too long, but at least in Finland, they are not distressed about seeking a new job. As a matter of fact, distress is something one can hardly detect in Kaurismäki’s corpus. No matter how dire and miserable the situations are, his actors’s poker face remains immutably impenetrable, and unlike “a deadpan look”, Kaurismäki’s trademark expression betrays no self-consciousness. His “subtraction” of emotions through impassivity and stillness of the body language is an acquired taste, but in FALLEN LEAVES, it reaches a form of abstraction, a simplicity, as we watch Ansa and Holappa masterfully code their intentions and thoughts barely pulling a facial muscle, it is droll, but also amazingly candid. Both Pöysti and Vatanen are real finds, especially the former, accessorizing her performative reduction with an evocative aroma of tristesse and resilience.Ansa and Holappa are two sides of the same coin, who mask the tediousness of their quotidian existence with a strong face of sufferance. However, when a chance to connect with someone arises, both are conferred with a volition to reach out (the lost contact part is very deliberate but how they wordlessly try is unexpectedly touching), even when fate separates them for a second time (after Holappa steels himself to get rid of his undue reliance on alcohol, a salient motif as a relationship deal-breaker in both films), it is merely another test for them to find each other (this time, it is Ansa’s turn to reciprocate her unuttered affection), walking side by side toward a probably rosier future. Kaurismäki’s concerns over class and politics continue its lifeline in both features (the ongoing report of Ukraine war is a running commentary in FALLEN LEAVES), so is his distinct sense of wry humor and his optimism in humanity, however gelid and reticent a person might intransigently appear, their inner benevolence can slowly radiate through and meld with a receptive equivalent. There is a knowing nod to Jim Jarmusch that much to Holappa’s amazement, Ansa really enjoys THE DEAD DON’T DIE (2019), a director whose artistic complexion is mostly akin to Kaurismäki’s, not least their fondness of using diegetic music, here, Kaurismäki’s Scandinavian auditory selection has always been a boon to salve one’s anomie-bedeviled anima. It must be a maxim that those who love Jarmusch’s films cannot be bad persons, and by the same token, so are Kaurismäki’s stalwarts. referential entries: Kaurismäki’s LE HAVRE (2011, 8.3/10); J-P Valeapää’s DOGS DON’T WEAR PANTS (2019, 6.2/10); Jim Jarmusch’s NIGHT ON EARTH (1991, 8.1/10).
English Title:The Other Side of Hope Original Title: Toivon tuolla puolenYear: 2017Country: Finland, GermanyLanguage: Finnish, English, Arabic, Swedish, JapaneseGenre: Comedy, DramaDirector/Screenwriter: Aki Kaurismäki Cinematography: Timo SalminenEditor:Samu HeikkiläCast:Sherwan HajiSakari KuosmanenIlkka KoivulaJanne HyytiäinenNuppu KoivuSimon Al-BazoonKaija PakarinenMaria JärvenhelmiNiroz HajiMilka AhlrothKati OutinenTommi KorpelaSulevi PeltolaPuntti ValtonenHannu-Pekka BjörkmanElias WesterbergTaneli MäkeläRating: 7.9/10
English Title: Fallen LeavesOriginal Title: Kuolleet lehdetYear: 2023Country: Finland, GermanyLanguage: Finnish ArabicGenre: Comedy, DramaDirector/Screenwriter: Aki Kaurismäki Cinematography: Timo SalminenEditor:Samu HeikkiläCast:Alma PöystiJussi VatanenJanne HyytiäinenNuppu KoivuMartti SuosaloMaria HeiskanenSakari KuosmanenAlina TomnikovMaustetytötSimon Al-BazoonRating: 7.7/10
10 ) 希望之歌
依然是熟悉的配方,原来的简洁,复古的摇滚乐,有故事的男人,外表冰冷,内心却一片澎湃,好人多恶人少,情节走向自然,但也真实展现了生活残忍的一面,不动声色的表演却掩饰不了内心的善良,热情,这个地处寒带的国家制度健全,却也十分冷漠。
喜欢这个风格,喜欢电影的结局,希望的另一面不是绝望,它是永远相信未来,以积极的态度面对,穷人命硬,从不会轻易放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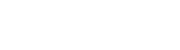



























第21届上海国际电影节2018.6.23衡山
好幽默,一大半都可以当喜剧看了。仍旧开场好久不出一句台词,不插些乐队演奏不舒服斯基。毕竟是阿基,剧情胡搞搞也可以接受,反正是超现实的调调来拍现实主义嘛。
熟悉的烤鸡味。奇怪的是,极简,冷色调,黑色幽默这些都是我喜欢的,但烤鸡的片却戳不中我
芬兰冷淡风,又包裹人情温暖,导演风格很明显
整部片都很丧,除了最后一点,全片几乎没人笑。每个人都表情严肃,但又很暖。剧情很悲伤,但中间的冷幽默又让人感到一丝的欣慰。
这效果感觉是几十年前的
考里斯马基看多了不腻不烦,是道好菜,就是想不起吃什么了就点这道菜的那种好菜。善良,真善良,真单纯,真温柔,导演是个好人。
两大男主在一个半小时的时候才正式碰面,碰面后画风立刻变暖萌,寿司店那段简直任性啊!
同样涉及新纳粹暴力和移民(难民)问题,这片冷冰冰的表皮下的人文关怀确实动人。比《凭空而来》那种靠臆想扭曲社会问题的垃圾片好多了。
沉重和轻快相间的难民电影。理想主义之下才能看到希望啊。
演技糟糕,剧情无聊。
冷峻,温暖,幽默 / 芬兰大师展@影城
浓郁的阿基气质!叙利亚难民感知人间冷暖 那家爵士舞曲环绕的餐厅 极简主义 出离戏剧化 停滞的表情 让我有种在看法斯宾德的错觉
看不懂的部分,看不懂。看得懂的地方,觉得很一般…
死太简单,我想活着。
面瘫冷漠的芬兰,基本代表了全欧洲对待叙利亚难民问题表面的怜悯背后的无情
人文关怀。
这个片子逻辑很神,小学生拍的……
这绝对是普通观众欣赏不来的作品,不幸的是,我正是普通观众。简洁的场景布置、直白的画面叙述、寥寥无几的台词、偶尔闪现的摇滚乐、我get不到的幽默点。能看出这是很独特的作品,也绝对会让资深影迷深爱的作品,可惜我竟然看困了两次,希望以后的我也能折服于考里斯马基导演的魅力。
别人评价很高,但是我看着没啥意思呢。有人说认识这导演,这我也没听说过啊。整部电影太过平淡,没有拍出难民的悲惨,有吃有喝还能天天抽烟闲逛,最后的妹妹莫名其妙从匈牙利跑到芬兰然后去自首了,这逻辑都不通。音乐很好,说幽默吧没看出来幽默,结尾还开放的。不知道到底是拍什么,难民片咋拍出喜剧呢。个人认为不是特别值得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