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驴叫》剧情介绍
伊欧最初是待在一支巡回表演的马戏团,那是它从小到大唯一的归属,后来它被迫离开,跋涉在波兰和意大利交界的乡间时又逃走,既遭受到残酷的状况,也遭遇到温暖的情况,而在这一路当中,它观察到人性的愚蠢和胜利。在伊欧的旅途中,它同时受到各种人物的帮助和阻碍,包括年轻的意大利牧师 (洛伦佐·祖佐洛 饰) 、女伯爵 (伊莎贝尔·于佩尔 饰) 及喧闹的波兰足球队等。热播电视剧最新电影金城档案天堂岛疑云第七季替身标靶第一季吾为君亡富贵逼人融和不容易第二季生命的荣耀多莉·帕顿的七彩圣诞:爱之圣环新网球王子U-17世界杯迷离警界:鬼车分歧者:异类觉醒暗黑之夜洛杉矶大暴乱囧蛋奇兵海豹突击队第七季真救世主传说北斗神拳尤莉亚传家庭主妇恐惧直播主竞赛戈德堡一家第六季摩登家庭第十一季凯利帮的真实历史生死不离新霸王花虎胆龙威4史酷比与蝙蝠侠:英勇无畏苏庆亮异形庇护所第四季爆燃战队奔奔者心理探险家
《驴叫》长篇影评
1 ) EO(微剧透)
人是最狡猾的,不然我怎么会能欺骗自己感受到了动物的感受。
EO在笼子里看车外草原上奔驰的马,它们再美丽,最后也只是人娱乐的对象。
EO观察动物,昆虫,人,自然,整个世界。
它大多数时候是沉默,不经意的叛逆,和旁观者无能为力的淡漠。
因为它看过无数被囚禁的动物,在它眼前被射杀或被电死的狐狸,被驱赶的牛羊,以及大家最后都同样的结局。
电影中,人成了附属角色,就像EO生命中的过客。
但是作者依旧给每一个人都赋予了独特的人物性格。
另外比较惊喜的是于佩尔也出演了。
影片中最震撼的就是EO出逃至森林的那段。
夜晚中森林的动物带给人危险的感受,但真正危险的其实是绿色的激光。
可是面对死亡过后,EO依然会阻挠树干上的蚂蚁。
就像它面对自己每天服务的马群们,也许有同情也有愤恨。
而同样,人类世界的戏剧性和人与人之间的邪恶也因为EO展现在我们眼前。
影片中的配乐有很多交响乐,也有配合人物的金属摇滚。
总之就是大多数时候听得人耳朵疼(可能跟放映厅很小有关),但是依旧非常惊喜震撼。
这是影片中的特色,也是艺术片的一种尝试。
然后巨响的音乐过后会有突然的寂静,然后又是巨响的音乐。
就跟影片中的其他片段一样,会有一小下一小下的惊吓和出乎意料。
还有值得一提的是影片应该是4:3的画面比例,很适合它,不知道变成其他比例会有什么感觉。
多视角的拍摄手法无疑是本片的根基,其他动物昆虫看EO,EO看人,人看EO,我们从EO的视角看EO所看到的世界。
有很多巧思和技巧但绝不是在炫技。
非常适合在电影院观看的电影。
2 ) 存在的就是有意义的
全片使用诸多POV镜头,向我们展示了驴的“视域”,而驴的“视角”——当它在看这些的时候,在想什么,获得了什么体验,对它有什么意义——是完全不可知的,这正如我们自己看到的天下熙熙攘攘的人群表象,我们有自己各自独特的体验,但终究不会完全理解任何一个他者的体验,其实动物的世界和人的世界就是是一个相互映射,相互象征的对应关系,驴的视角其实就是套着枷锁的人的视角,收获自由前,它仅仅是只供人取乐的玩物,逃离束缚后,它不过是只无家可归的野驴,在人生的平凡之路上多的是快乐与恐惧,未知与渴望,成功与无奈,美好与邪恶…这让人想到了海德格尔的畏与烦,叔本华的痛苦与无聊,踏遍惊险刺激游历人间的每一步脚印而从不放弃纯真,或从捶打后的昏迷中慢慢苏醒,继续在茫然中寻找出路,或在惶恐中的迷雾中踽踽独行,终究在命运中找寻归宿,但无论遭遇什么,他终将自己走出自己的生活道路,因为存在的即是合理的,存在的就是有意义的!
3 ) 一场缓慢坠入深渊的悲剧
近年来有不少出色的动物题材影片吸引着观众的眼球,这些作品借助拟人化的手法,从动物的视角去展现它们的世界与生活,给观众带来反思,从而引出各种炙手可热的现实议题。
其中《贡达》和《奶牛》可谓大胆破格的尝试,一举颠覆了常规的动物纪录片范式。
去年戛纳又出现一部动物影片,不仅拿下评审团奖,更在年末登上不少年度十佳榜单,实力惊人。
这部《驴叫》出自波兰资深导演杰兹·斯科利莫夫斯基之手,这是他相隔 30 多年后重返戛纳竞赛。
据他所言,新片致敬了电影大师布莱松的《驴子巴萨特》,这部经典电影当年让他在电影院感动落泪。
而他这部致敬之作沿用了原作的公路片形式,表现一头驴在不同主人的手中流转,却不止于将其颠沛流离的命运展现于观众眼前。
影片借助驴的视角引出形形色色的人物(动物保护团体、极右翼分子、动物走私集团、没落贵族等),揭露当下欧洲错综复杂的社会问题,令其有了更开阔的视野格局,这也是影片高于《贡达》和《奶牛》之处。
以上两部动物纪录片的过度拟人化处理,实则暗藏着人类自作聪明强加于动物身上的意识,但事实上动物的真实意识人类并不通晓,正如动物也无法理解人类的行为,而这部《驴叫》另一个高明之处便将这层意义表达出来。
全片并非由动物的主观视角贯穿始终,而是将之与人类视点彼此交错呈现。
在呈现动物视点之时,更动用不少特殊的美学手段,比如红色滤镜、无人机拍摄,以及梦境里的镜像角色,营造出一种神秘的气息,点明了一个不容忽视的事实:驴的行为意识无法为人类所知,尽管很多时候它表现出乖巧驯服的一面,但下一秒它又可能将你踢倒在地而不省人事。
在两种视角交织下的公路类型叙事,编织出一幅时而饱含温情、时而荒诞可笑的人生百态图。
这也许轻易让观众得出结论:在淳朴善良的驴的面前,人类总是愚蠢傲慢的物种。
不过,这依然是人类自以为是的无端猜测,而在导演看来,不论驴也好,人类也罢,似乎都无法扭转自身的命运,一步一步缓慢走向悲剧的深渊。
导演这种执拗的悲观主义倒是抓住了这两种生物的相似性,并流露出他对当下欧洲社会每况愈下的慨叹。
4 ) 长评 | 心理表现主义的幻觉:《驴叫》《金发美人》对比批评
文 / Annihilator
《驴叫》(EO, 2022)乍一看是前两年的两部“动物电影”——《奶牛》(Cow, 2021)和《贡达》(Gunda, 2020)——的一个系列性的延续,但实际上,它更像是同年的另一部电影《金发美人》(Blonde, 2022)的某种镜像。
驴叫 (2022)6.92022 / 波兰 意大利 / 剧情 / 杰兹·斯科利莫夫斯基 / 桑德拉·德拉兹马尔斯卡 伊莎贝尔·于佩尔
奶牛 (2021)7.82021 / 英国 / 纪录片 / 安德里亚·阿诺德
贡达 (2020)7.22020 / 挪威 美国 / 纪录片 / 维克多·科萨科夫斯基为了理解这一点,我们不妨把观众看电影时对人物投出的目光粗略地划分为两种:一种是从观看的主体到被观看的形象之间的单向的看,用泛女性主义语汇来说就是“凝视”;另一种则是代入式的看,让我们与人物站在一起、分享他们的视角,以他们为中介去看周遭、去看这个世界。
连接起世界上曾经最著名的影星和一头被马戏团卖掉的驴的,正是第二种看的缺失,视角的缺失。
自居为唯一拥有意识的“高等生命”的我们从未分享过一头驴的视角,正如自居观众(=“消费者”)的我们从未分享过玛丽莲·梦露的视角:作为演员,她最成功的、也是《金发美人》中频繁引用的几部电影——《七年之痒》(The Seven Year Itch, 1955)《热情如火》(Some Like it Hot, 1959)以及《绅士爱美人》(Gentlemen Prefer Blondes, 1953)——不正是仅仅建立在第一种消费式的目光之上的吗?
《金发美人》中的《绅士爱美人》首映会如此,对缺失的视角的找回、重塑和重新分享,就成为了女性主义和动物保护主义共通的一个迫切问题,也构成了《驴叫》和《金发美人》的原初动力。
如何创造和分享视角?
在以女性为主人公的电影中,《旺达》(Wanda, 1970)《首演之夜》(Opening Night, 1977)《托尼·厄德曼》(Toni Erdmann, 2016)《在你面前》(당신얼굴 앞에서, 2021)是一组很好的范本。
这四部电影所处理的题材和主人公所在的阶级各不相同,但它们都非常成功地邀请我们进入主人公的个体化的视角,向我们分享了她们对于生活、对于周遭、对于整个世界的体验。
这一成功显然是基于一种电影的叙事传统(在这里传统二字绝非贬义):在设计与即兴之间平衡的剧本写作、表演、拍摄铺设出了充满真实细节的“情境”,而借由情境,我们得以充分地认识和理解主人公的处境、行动和情感,进而产生共鸣。
以这种叙事传统为前提,第二种看会在第一种看的超越性的延伸中出现:在《旺达》结尾的那张动人的停格影像中,当我们将目光投向芭芭拉·洛登,我们不只得到了一张忧郁得非常美丽的脸(第一种看),而且因为我们已经跟随她经历了一整部电影的起起落落,因此在这里,我们进一步分享了她对世界的沉思和痛苦,分享了她的忧郁本身。
《旺达》结尾的停格然而,我们很容易发现,在《驴叫》和《金发美人》中并不存在真正意义上的情境,它们的叙事都是松散而琐碎的:前者和它的致敬对象《驴子巴萨特》(Au hasard Balthazar, 1966)一样,驴子不断在不同人之间转手形成了一个类公路片的结构,串联起人事的不同片段;后者虽然回溯了传主的情感和事业史上所有重大事件,但并没有深入其中任何一个,而是用意识流一般的结构将它们拼贴起来。
如此一来,观众如何分享主人公的视角?
《金发美人》给出的答案是:直接用影像去模拟人物的感知,模拟他们所看到的世界。
这种模拟,显然是一种心理学角度的模拟,而不是现实主义的:夸张的镜头角度、光线、色彩、升格、镜头变形、不断变换着的画幅和色彩格式,电影通过这些介于纯粹的生理感官冲击和模糊的象征主义之间的技法,试图向我们展现梦露对于现实的有别于常人的知觉,这种知觉恰好符合了她受压迫者的身份,符合了她“在父权制的社会结构和好莱坞体系中、在男性凝视中感受到的压力”。
《金发美人》中镜头变形尽管《金发美人》从技术层面可以说是现代电影工业的最新结晶,但这种心理学模拟方法,也许比前述的电影叙事传统更加古旧:我们难道不是在苏联学派,在爱森斯坦(Sergei M. Eisenstein)的剪辑或卡拉托佐夫(Mikhail Kalatozov)的摄影调度中,就已经见识过这种添油加醋的夸张技法了吗?
卡拉托佐夫《我是古巴》中夸张的镜头角度姑且可称这种方法为“心理表现主义”:将人物的感知、情绪、思维活动等等一切心理现象,都转化为影像上的某种夸张、反常、扭曲。
梦露的童年回忆、梦露的三角恋情,梦露的片场和首映会,梦露的家庭生活,以及最终,梦露的死亡——无一不是以这种表现主义来完成组织的。
《金发美人》的结尾的叠印然而,表现主义对心理的模拟永远只可能是一种幻觉。
一部电影可以不将叙事作为重心,甚至完全没有叙事;但同样,一部不在意叙事的电影也不可能有人物,更不可能创造人物的视角。
只想用一些花哨的电影技巧就去定义一个人物对世界的体验,这是一种虚伪,也是一种独裁。
一切表现主义技巧,无论是通过暴力的生理刺激还是肤浅的象征主义,它们所获得的都只是单义的情绪、单义的理解、单义的印象,是一系列能指与所指之间的刻板等式:虚焦=意识模糊,镜头畸变=精神创伤,眩光=刺眼,广角=恐旷症,对称构图=秩序压迫……这一系列等式非但没有真正分享人物的视角,反而反过来将本应该复杂的、流变的人物也化约、降维、解构为这些单义的能指碎片的集合。
《金发美人》中的对称构图《金发美人》根本上的虚伪性也正是在这里体现出来:它看似是在为梦露夺回失去的视角,但观众看完绝不会对梦露产生新的理解(也即,一种脱离了非黑即白的道德判断维度的,辩证的、具体化的理解),反而只会得到“梦露的恋父情结造就了她悲惨的一生”这一种庸俗版本的精神分析结论。
“父权社会的受害者”这种“新定义”,相对于“金发胸大无脑女郎”这种“旧定义”,仍然是非黑即白的,所谓的革新只是将黑的变成了白的,仅此而已。
在这里,人物仍旧不具备最基本的主体性,仍然是第一种看的绝对对象——只不过色情的看变成了怜悯的看,但本质上都是同一种猎奇,同一种窥淫癖。
不若说,《金发美人》是一份打着女性主义旗号的八卦小报(而电影的原著事实上也的确使用了许多未经证实的传说),四处打满了“震惊!
”“原来……”的标题,如果说它真的有揭露好莱坞父权体系的罪恶(实际上也很浅薄),也只是想通过揭露来获得猎奇式的震撼。
更可怕的也许是,观众甚至不会得到“梦露的恋父情结造就了她悲惨的一生”;更多吹捧它的人的理由仅仅是“哇!
这部电影拍得好新奇!
好壮观!
好‘美’!
”这是一种怎样可怕的本末倒置和二次消费?
于是,我们发现《金发美人》最真实的身份只不过是一部Netflix电影:正如导演安德鲁·多米尼克(Andrew Dominik)在访谈中展现的对于梦露职业生涯的彻底的无知一样,在一部Netflix电影(或者一部A24电影,以及更多类似的企业)中,任何社会议题都只是资本主义电影工业生产线——投入资金、缔造奇观、收获消费——上的借口。
前文对这种表现主义的定义是“用影像去模拟人物的感知”;在此我想推翻这一定义。
这不是影像,而仅仅是“视听”——一个更加技术性的词语,它暗示着一种对电影的好坏的判断标准:越精致、越夸张、越华丽、越复杂、越体系化、越“风格化”、越奇特、越有技术难度,就越好,越“有视听”;而也恰恰是同一种判断标准,否定了选择了朴素和简洁的《托尼·厄德曼》或洪常秀的任何一部电影,认为它们“没有视听”,因此不是电影,而是电视剧或者VLOG。
《托尼·厄德曼》朴素的影像被人诟病为“电视剧”然而,“视听”并不是电影,不如说它的近义词是所谓的“电影感”:《金发美人》正和许多当下流行的“精致电视剧”(不用怀疑,其中很多正和《金发美人》一样来自Netflix)一样,“很有电影感”,但与成本仅十万美元的《旺达》或《在你面前》而言,它的一切砸钱式的炫技都显得如此拙劣可笑。
尽管在《驴叫》中也有不少“心理表现主义”的运用,如刚一开场马戏团段落闪烁的红光和断裂的剪辑,又如“驴眼”所看到的升格的奔腾马儿;但它和《金发美人》还是存在一个关键区别:如果说《金发美人》企图用庸俗化的弗洛伊德主义和女性主义去定义梦露的视角,并且这种企图最终获得了完美的成功(在电影的结尾,死去的梦露与娇媚的梦露的叠印用一种令人作呕地确证了这一点);那么《驴叫》则出发于定义的尝试,但最终却用一整部电影证明了这种尝试的失败。
《驴叫》中的马儿奔腾镜头在这头名叫EO的驴从马戏团一路辗转到屠宰场的旅途中,我们虽然始终跟随着这头驴,但我们真的分享了它的视角吗?
全片使用的诸多POV镜头,仅仅是向我们展示了驴的“视域”,而驴的“视角”——当它在看这些的时候,在想什么,获得了什么体验,对它有什么意义——是完全不可知的。
如果你碰巧看过一些宠物主人给猫咪或者狗狗穿戴录像设备拍出来的那些POV短视频,就会理解我在说什么。
在《驴叫》中,无论是前述的马戏团段落、升格的奔腾马儿,还是驴静静地吃草、在路上小跑、站在水坝的桥上的那些时刻,我们都不可能真正进入驴的视角中;它是不可穿透的,拒绝我们自以为是的投射。
《金发美人》向我们分享“梦露的视角”,是为了让我们从她看到的外部世界去理解她的内心世界(创作者所粗暴定义的内心世界);而《驴叫》向我们分享“驴的视域”,只是通过这种视域的陌异让我们深知驴的视角的不可代入,正如反过来,EO也常常对片中出现的人类段落表现出一种“不理解”、“与我无关”的态度。
《驴叫》中EO站在水坝前如果说真的在某些时刻,我们仿佛感知到了驴的心理,那也并不是通过那些肤浅的心理表现主义的符号,而是通过一种库里肖夫效应,这一点可以在斯科利莫夫斯基(Jerzy Skolimowski)的访谈中得到印证——先看到这个世界,又看到了驴的反应,然后冥冥之中将它们连接了起来——并且这种库里肖夫效应是流动的、脆弱的、不确定的,始终保持着神秘和新鲜,不会落入某一种具体的定义之中。
《驴叫》中多次在拍完环境后拍驴的眼睛比较《驴叫》中的EO之死与《金发美人》中的梦露之死,这一点会更加明确:《金发美人》不仅将梦露死因设计为一个伏笔(父亲的信),而且还在死前给出了大量的闪回,进一步确保了我们将她的死理解成一种受难,一种精神分析的创伤重现;而《驴叫》中,EO跟随牛群进入了屠宰场则出于一种令人难过的偶然性,而它自己也完全处于一种懵懂茫然的状态(电影在这里可以闪回马戏团女演员的片段,但没有)。
它对这个世界的观察,正如我们对它的观察一样,是一个不可理解的黑洞。
《驴叫》结尾的屠宰场这正是斯科利莫夫斯基的作者性在《驴叫》中的延续:尽管几十年过去,他的电影的风格和技术都已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但他对人物的态度始终如一。
EO就像《深水》(Deep End, 1970)中的男孩和女孩一样,是始终无法看清、看透的形象,拒绝被定义、被解构。
《驴叫》的失败之处也就在于,很多处仍不得不使用大量音乐和闪回来尝试解释EO出走的动机,如果把这些连带马戏团女演员的所有情节一并删去,只展现EO在这个世界漫游的过程,也许它有机会成为杰作,成为驴版的《唐吉诃德》(Honor de cavalleria, 2006)。
《深水》中的男孩与女孩但即便是现在这样,《驴叫》也依旧比《金发美人》好太多,从片名上就可以发现端倪:“Blonde”无论取其刻板之义还是反讽之义,都是一个单义的、强目的性的概括;而“EO”,无论是驴的名字,还是驴叫的拟声词,都是一个隐匿了作者目的、无机的词语。
从这一点上看,斯科利莫夫斯基的确继承了布列松(Robert Bresson)的命名之道——《乡村牧师日记》(Journal d'un curé de campagne, 1951)《扒手》(Pickpocket, 1959)《驴子巴萨特》或《武士兰士诺》(Lancelot du Lac, 1974)——如此简洁。
5 ) 可怜的EO
EO,一头杰兹·斯科利莫夫斯基的工具驴。
开头迷幻灯光,搞得的好像人兽X情节,然后就是一个精神不太正常,至少看上去是自己养活不了自己的姑娘,用一块胡萝卜杯子蛋糕,骗了一头驴的感情。
驴本来挺好的,从马戏团解放到一个小农场,马戏团里它瘦骨嶙峋,农场看起来规模也不大但是至少没虐待它,但是,一头驴决定不了一部电影的走向,它被导演安排去追一个人类,在一个月黑风高,路上出现了被水冲走的癞蛤蟆,死掉的狼?
活的乌鸦,人看起来会很怕,但是驴怕不怕另说的一段路,总之,导演觉得驴也是会怕这些的。
人类的世界怎么会有一头驴的思想空间呢,驴果不其然的被牵扯进人类的纠纷,被打进了动物医院QAQ ,好不容易休养过来,导演加了两个回溯镜头,驴又必须为了那个姑娘的胡萝卜杯子蛋糕上路了。
二次被人类一厢情愿的拐跑。
最后被一群牛羊挤着混进了一个农场。
可怜的驴,导演还是继续拍<<与安娜的四个夜晚>>这种纯人类的电影吧,别来霍霍动物了。
6 ) 《驴叫/伊奥》
【在城市中穿行,在田野里奔袭,以生灵之眼看人类姿态。
】
《驴叫/伊奥》温柔的手抚过伊奥的皮毛,双手自背脊而下直达四足,动作伴随着观众们的热烈呼嚎停息,光芒熄灭,走入黑暗的后台。
这是伊奥的每一天,伊奥是马戏团里的一头毛驴,尚未长成的伊奥在被马戏团长期鞭挞之外,还有女主人的温柔相伴,身着红裙的女主人每日都抚摸着它的身躯,以嘴唇相贴。
这一切伴随着现代法治的完善而终结,马戏团因为虐待动物被警方关停,动物保护组织对着团长叫嚣、咆哮,而伊奥则在女主人的面前被警方带走。
在离别后,伊奥被卖到了一处养马场,高头大马英姿飒爽,平原上到处都是他们奔袭的步伐,但到了夜晚,伊奥还是与他们一同生活,伊奥看着那些高头大马被洗刷,但它却连理顺毛发的手都未曾拥有。
马儿们于马厩中嘶鸣,看着它们被管理员安抚,伊奥拉动捆缚于身的枷锁,带动着小车前进,拉倒了置放奖杯的货架,随后,伊奥再次被卖掉。
伊奥被卖到了一处农场,里面如它一般的驴子层出不穷,他似乎找到了归属,但它心中一直思念着自己曾经的主人,在夜晚所畅想女主人的抚摸。
不知过了多久,在一天夜里,那早已不见的女主人又出现了,她隔着篱笆抚摸了伊奥的头,拿出胡萝卜蛋糕庆祝伊奥的生日,但因为女主人有自己的生活,最终还是远走高飞。
伊奥见女主人远走,立刻跳出围栏,冲进森林里探寻那若有若无的痕迹,但森林中的危险远远超出它的预期。
深夜中的森林只有湍急的流水与狂风吹拂树梢的声音,猫头鹰在树枝上伺机而动,狼群在远方嚎叫,森林中的动物皆保持警惕,只有伊奥无所察觉的前进。
身边狂风四起,远处的镭射光刺破黑暗而来,追随其后的枪声击杀了即将扑向伊奥的野狼,伊奥快步逃开,只留下背后追踪群狼踪迹的人们。
伊奥穿越下水道、迈上青草峰、看向鲜红朝阳、朝着一无所知处前进。
伊奥在早晨到达了一处小镇,它站在一家鱼缸店前踌躇良久,最终不停嘶鸣,这引来了消防队的追捕,他们抓住了伊奥,把它锁在消防车后面前进。
在消防车停下,一个无政府主义者前来解开了绳子,混乱就是他所想要。
伊奥无处可去,于是继续向前流浪。
在小镇的角落,有两支足球队真正抗衡,比赛已经到达了最后阶段,最后的一个点球将决定胜负,伊奥询声踱步而来,看向赛场上的球,最后的点球环节因为红方队员的失误而结束,蓝方告捷而归,他们看见了赛场边的伊奥,于是带着它在小镇的每一个角落传播喜讯。
他们带着伊奥到了一家快餐厅,在餐厅里肆意狂欢,喧闹的咆哮令伊奥不适,它走出餐厅,在草地旁停留。
而白天输掉的红方队员似乎并没有什么道德,他们拿着武器气势汹汹的闯进蓝方的聚会餐厅,打砸一切,所有人都被打倒,餐厅遍地狼籍,但显然这群人并没消气,他们还找到了在一边旁观的伊奥,用棒球棍把伊奥打到濒死。
濒死的伊奥并未结束痛苦,它被兽医带回医院治疗,被击打而出的鲜血与伤痕遍布其身,它回忆着女主人的抚摸,对比着温柔与暴力,眼眸中活力黯淡。
医生本想对它实行安乐死,却意外被兽医院里面的清洁工带走,伊奥恢复了活力,它还是拉车,但它这次拉的不是货物,而是动物的尸体。
救走伊奥的清洁工是个盗猎者,他抓捕狐狸然后把它们关进笼子里电死,然后取走他们的一切。
狐狸们在笼子中哀嚎和嘶叫,伊奥倾听着,趁清洁工弯腰,一脚踢中他的面部,这一脚直接击碎了清洁工的脑子,他就此死去。
在多次转手后,伊奥最终被卖到香肠厂里,它被关在了通往工厂的货车上,它以及货车上其他的马儿,将被做成香肠,对于前路一无所知的伊奥跟着司机奔波了几个日夜。
直到在一处加油站里,司机被非洲逃来意大利的难民给割喉,但他们没有拿走任何东西,只是因为司机开了个黄色玩笑。
当司机的尸体被发现后,伊奥也被暂时绑在了电线杆旁边,一个颓废萎靡的青年走来,向伊奥打招呼。
他偷偷带走了伊奥,回到了自己的家乡,但这个青年回到家乡的原因,是要和自己的继母苟合,他的父亲早已去世,他垂涎继母已久,在这次归乡后终于如愿以偿。
正在院子中的伊奥看见大门陡然敞开,它默默的离开了院子,走向了无边原野,跨越了倒流的河水,行至不知名的远方。
而伊奥的结局也已注定,在原野中漫游的伊奥混入了牛群,在牧牛人的驱赶下进入了屠宰场,伊奥走在最前面,仿佛迫不及待的追求死亡,于是他前进,走向了无边黑暗,随着穿刺皮肉的声音响起,伊奥的旅行也戛然而止。
【END】
接下来是我的看法这是一部台词非常少的电影,主角是名叫伊奥的驴,我们借用伊奥的眼睛观察世界,看向近几年来越来越严重的社会问题。
极端动物保护组织、无政府主义者、犯罪的偷渡客、因为输球而暴动的球迷、盗猎者、以及一些复杂的伦理问题,电影的主要地域是波兰,但影射的却是整个欧洲和北美洲,两个地域人民的参差被折射在荧幕上,用一匹不会言语的驴做引子而展开。
但在展开社会问题的同时,电影也并没有冷落伊奥,在伊奥本身上,导演使用了大量的心理蒙太奇,用各异的机位和特效拍摄旅途上的伊奥,来凸显一只驴的心理状态。
原文片名"EO"是驴主角的名字“伊奥”,同时也是它叫声的拟声词。
观众于是跟随它的视角,看见动物眼中的世界为何种模样,并借过程中伊奥与不同人的萍水相逢,展现人性为何物,也揭露着对于非人类的它们而言,所处的世界又是一个什么样的地方。
同以驴子作为主角,不免令人想起法国导演罗伯特·布列松1966年的作品《驴子巴特萨》,两者都呈现一头曾被深爱的驴,最后被暴力对待、终究走向死亡的旅程。
但跟前者不同的是导演的拍摄手法,电影本体中在各个地方采用了大红色的滤镜,刺目的红光配合心理蒙太奇,把电影的意识流提升到了一种很极端的地步。
但就算这样的拍摄,也令我这种人无法和伊奥共情,《夏洛特的网》中的两位主角动物是加上了人类的感情才让电影感人,但这部电影之中的伊奥是完全没有任何对话的,呆愣、木讷,无法体会的动物的感情只能通过意识流镜头和对女主人的回忆管中窥豹。
但这正是导演高明之处,人不需要也无法理解动物的感情,我们所看到的,也是我们强加的感情,包括我写的文章,只是我心目中的伊奥,真正以伊奥视角出发,谁知道它究竟想什么呢?
7 ) 用他者看世界
用驴子,加上公路电影,来看人情世故,见证生命的历程,这本身就是一个很有趣的生命体验不用太多语言,矛盾冲突更多的放置在人之间的情感冲突,让一个看似动物电影,却多了更多的人味儿,红色的低调,让生命更加张扬,把故事和电影语言结合,我想做的恰到好处。
电影是有语言的,除了故事好看,更多的是你可以在每一幅画面里呼吸到不一样的电影空气。
8 ) 你会绑架一头驴吗?
我会高喊无政府主义万岁,解绑它,让它思考,再让它跑。
“没选择的先死,有邪念的再死,不坚定的后死。
”——————狠狠的跟一头流浪的驴共情了。
那些猩红色镜头下自由的指代:能奔跑的马,大型的发电机组,机器狗,喷涌而出的水坝,帮助女孩的司机和离家出走的公子哥。
它们看似简单且能轻松的摇曳,但实际上:被限制着方向和速度,依着风转动,由人遥控,被阀门阻止,被欲望操作,被现实绑架。
而它带来的也无一例外都是停止和死亡。
Eo被绑架,松绑,再绑架挣脱,它逃出去了那么那么多次,是为了信仰。
Eo挣扎了又妥协,最后还是缓缓走进了屠宰场,是妥协。
当然Eo最终也停止和死亡了,although he is not a fucking horse,好消息是他应该会变成一碟好吃的驴肉salami。
当然他也未曾流浪。
是要 做高高在上的政治家?
做伪教徒?
做帮派中伤害一头无辜的驴的施暴者?
还是做为信仰奔跑又对现实妥协的驴?
做一个向着信仰坚定的奔跑的自由人吧,即使看不到终点,至少还能活久一点。
心有所念,乘风破浪,机遇自会至。
信仰虽不是免死牌,但愿不枉此回人间游。
——————这个电影还有一点credit要给这头驴,演的太好了……
9 ) 驴眼看世界
有时我也会幻想自己是一只动物,包括一头驴。
从驴的角度看这个世界,充满了不解与荒诞,甚至和我们看动物没什么不同。
人类总是喜欢扮演各种角色,时而扮演救世主试图普渡众生,时而扮演圣斗士争得面红耳赤,总是做着实际上毫无意义的事并且始终乐此不疲。
这样看来和驴也没什么不同,毕竟驴的一生也是在随波逐流似的漂泊;甚至还不如一头驴,驴至少不会为了无意义的事焦虑不安。
但是和驴相同的是,人最终的归宿也是屠宰场。
或是被颐指气使的老爷们屠宰,或是被自己一直看不上的仆人们屠宰,或许当自己倒在血泊中的那一刻,才能真正明白自己毫无意义的一生多么荒诞,多么毫无意义。
当自己找寻不到人生的意义的时候,不妨去看看动物们,毕竟人也是动物的一种,在地球眼中,并不比其他动物高贵到哪里去。
实际一点,淡然一点,不要赋予人生太多的意义,人生的意义就是过程本身。
10 ) 电影评论《驴叫》:“巴尔塔扎尔”的神圣幽灵
在写了一段时间影评之后,经常会有人问我,是不是看过了很多电影。
其实没有。
我曾经很多次想改掉一周看一部电影的习惯,但好像阅片量也没什么显著提高。
我选片的逻辑性不强,主要看网站更新的电影与我生活发生了怎样的关联。
比如奥运会时会想看《红气球之旅》,又因为侯孝贤写了《刺客聂隐娘:以画绘诗》。
这次看《驴叫》,完全是因为《刺客聂隐娘》的一幅剧照所引出的一句谚语:“赋得于灞桥风雪驴背上”。
不过这头叫“EO”的毛驴完全没有踏雪寻梅典故中毛驴的浪漫气质。
甚至可以说它的境遇相当悲惨,看到一半的时候我的内心就已备受煎熬。
那种感觉就像在读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白夜》。
曾经听一位俄国导游说过一个关于什么是俄罗斯文学的笑话:需要一个条件,要么读者受折磨、要么作者受折磨、要么就是主人公受折磨。
而如果这三位都受折磨,那它就是俄罗斯文学的杰作。
确实,在我看来这部电影非常优秀。
只是按照杰作的“标准”还要看作者是不是备受煎熬(笑)。
于是我去查了一下影片的导演。
杰兹.斯克利莫夫斯基是位年过八旬的波兰老者时,我瞬间就明白了为什么电影要用一头驴来表现一个让人绝望的世界。
回顾近八十年的波兰,那是一个被二战炮火洗礼,先后被德国和苏联瓜分的国度。
在宗教上波兰曾被誉为天主之矛,欧洲之盾,抵御过来自各方异教的威胁。
还曾经将上帝加冕为波兰国王,算得上是世界上最笃信上帝的国家之一。
而在圣经中驴子的形象又经常和耶稣联系在一起。
在圣经中,耶稣骑驴抵达耶路撒冷的场景寓意深刻。
象征着和平进入耶路撒冷,表明耶稣带来了和平的信息。
这一场景不仅展示了驴作为交通工具的实际用途,更强调了耶稣的谦卑和顺从,以及他对人类救赎工程的重视和参与。
这场救赎工程可谓工事浩大,从公元1世纪一直延续到了19世纪世纪尼采喊出了那句惊世骇俗的“上帝已死”。
于是在下一个世纪里我们不再能从电影里直接看到信仰上帝的世界,而只能借一头小毛驴之眼对这个失去信仰的世界做一次临终前的回眸。
第一次用这个办法将上帝与毛驴关联起来的是杰兹导演的前辈罗伯特.布列松。
1966年他拍摄了电影《驴子巴萨特》(又名《巴尔塔扎尔的遭遇》),《驴叫》就是对它的致敬。
更准确地说算是它的续集。
因为“EO”眼中呈现的世界便是如今这个“上帝已远”的世界。
在“巴尔塔扎尔”上映时,欧洲大陆尚有一丝上帝临走时留下的余晖。
在巨人复苏的年代,信仰的遗产就像汽油,驱动着欧洲的再度崛起,而付出的代价就是燃烧时排出的尾气,混合着曾经醇厚与虔诚的情感一起成为巨人脚下扬起的烟尘飘散而去。
唯独留下几粒不肯燃尽的“残渣”。
这些残渣里肯定有布列松的影子。
他肯定也想在离开之前再看一眼这个“上帝已死”的世界。
遗憾的是,它并没有在当时人类选定的两种路线中看到任何希望。
也许是因为人类自身的原罪还尚未赎清。
于是借“巴尔塔扎尔”之眼我们看到,无论是象征着新技术与未来的开汽车的青年们;还是象征着自然与传统的坐驴车的安妮一家;乃至被视作革命性力量的无产者阿诺德全都不一而足地如摩西十诫中描述般“恶贯满盈”。
即便如此,我们还能从《驴子巴萨特》里发现最后一丝温存。
至少片中的母亲们都还如玛丽亚般保有母性的光辉。
可50年后“EO”眼中的世界里这最后一缕温暖也荡然无存。
这并不意味着母爱已经远去,而是家庭作为共同体社会的最后一处堡垒已经在晚期资本主义的欧洲社会中被瓦解。
于是我们在《驴叫》中看到了一个《钢琴教师》中的伊丽莎白.于佩尔。
一个外形出众气质、独特的母亲。
但同时又专制无礼,对自己的儿子想入非非。
葛兰西曾经说过:“旧的世界正在凋零,新的世界却还在挣扎着诞生,现在是妖魔鬼怪的年代。
”这句话在“巴尔塔扎尔”的时代仿佛准确地预言了人类社会的未来,但对于生长在“EO”时代的人来说,中间的一句话则应当划去,新世界难道不就是现在的世界?
难道还存在过另一种可能性?
这种断裂就如同我第一次看《驴叫》之后的感觉。
如果我不是因为没看懂而又去看了《驴子巴萨特》,我完全无法将“EO”和“上帝”联系在一起。
而显然这种断裂并非只在宗教意义上的,而是普遍于社会的历史语境中。
就像巴黎奥运会的开幕式那样,对于20世纪历史的空白书写,对萨特、戈达尔、加缪、福柯等等一批青史留名人物的遗忘正是如今意识形态工程的基本策略。
在《驴叫》里我们目睹了这种历史断裂下的世界:一头被人道主义之名所救下的驴子,正在人道的世界里遍体鳞伤。
就像资本世界里的一种特有面貌,一边说着经济状态良好,民主自由开放;一边街头难民流行。
显然在这种框架下的“人道主义”完全失去了从上帝手中接过拯救世人的能力,而俨然成了拯救这个破损世界的粘合剂。
显然,这种虚假的人道主义是去政治化,去历史化之后的产物。
然而是否还有一种可能来避免更多的“EO”出现?
如此切实又如此宏大的问题也许真的是“上帝”应当思考的问题。
也许正是带着这个问题,“上帝”借“EO”之躯完成了一次哈姆雷特式的幽灵归来。
只是此时“上帝”已经不再保有“巴尔塔扎尔”世界里的最后一丝祥和,而成为了阿甘本笔下的“神圣人”——苟延残喘的赤裸生命。
(“神圣”:在古罗马的宗教中,“神圣”指与普通社会分离开的人或物,一旦被“神圣”就丧失了所有的民事权利,也不能参与宗教活动等。
)
遗憾的是这个再无任何拯救力的“上帝”自己都变成了一个有待拯救的对象。
他再也无法从同样被囚禁的同类中看到“巴尔塔扎尔”眼中凶狠的老虎、猿猴、北极熊,取而代之只有被驯服的温顺的马。
甚至当他阅尽了人间疾苦想要返回天堂都已变得不再可能。
让我们回顾两部影片的结尾。
“巴尔塔扎尔”最后死在了羊群包围宛如云朵的“天堂”了,而“EO”则活着走进了牛群包围的屠宰场中。
是的,他再次归来的世界就是这样一个世界,一个即使你生活在“屠宰场”里,但都无法离去的世界,一个从驴子眼中反射出的即魔幻又现实的世界。
在著名的魔幻现实主义作家卡彭铁尔和马尔克斯看来,魔幻现实主义的模型,其得以成立的可能性,正源于其内含着具有结构性断裂的某种原始材料。
不绕弯子地说,魔幻现实主义与新生期资本主义或其科技面貌之间的重叠与共存。
从这一视角来看,魔幻现实主义电影的构建逻辑就不是大众电影的诉说方式而是另一种截然不同的生产概念,具体来说就如同福柯所言:“人民的记忆某种意义上是对抗历史的场域。
”又或许,在一位成长在波兰历史中的导演,一位用自己的记忆抵抗着历史言说的导演的眼中,现实的世界必然如“上帝—EO”眼中那样,只能是即魔幻又现实的世界。
诗人威廉.巴特勒.叶芝在《基督再临》的中曾描述过这样的世界:暗红的潮汐正四处弥漫,为纯情举办的祭仪已被淹没;最优者再无信念,最劣者激情澎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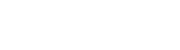











































































(7.7/10)布列松看待世界的眼光冷酷中带有一丝悲悯,Skolimowski则更残忍也更愤怒:所有的动物都活在人类的剥削之下,而人类的世界里尽是混乱、无序、不公。Balthazar与EO都以死来摆脱世间疾苦,实现真正的自由。然而Balthazar的死是被动的、无奈的,也许他觉得自己时候未到;EO的死却是主动的,他对于这个世界早已失去了任何留恋,便心甘情愿踏入黑暗。
很可爱的毛驴。lorenzo出场后和毛驴的戏份都挺可爱的,“我这算是救了你,还是拐了你啊?”哎哟喂 去看了幕后采访男主角(驴)主人家的视频,笑死我了,Tako对他的替身驴演员之一Hola一见钟情,“All he thinks about is sex!!”哈哈哈哈
有点儿戏
想说的太多 但其实都没说明白
如果我没猜错,EO 这个名字在这里表示 Europe
TIFF2022|观影29|有生之年在IMAX厅看《EO》今年心满意足了!满场!这什么重工业现实魔幻主义动物公路电影!没想到“我从没看过这样的电影!” 竟然有一天会从我的嘴里说出来,电影的第一镜就让人热泪盈眶!好久没有电影让人这么激动了!导演的音乐品味爱了!里面的运镜灯光摄影拍摄剧情无可挑剔!我今年TIFF想投一百票的电影!也是今年影片结束需要赶紧把眼泪憋回去的几部电影之一!
好多次觉得导演拍活人挺带劲然后猛然想起片子的主角是驴,不得不给驴几个特写配点煽情音乐。反复几次后倍感疲惫,踏踏实实拍人就好了,为啥非要拽上一头驴,这么累就为了去电影节得奖嘛?音乐用的实在太糟糕了,听的百爪挠心。
又吵又投机
真正的在把驴当成角色在拍,有很多驴的主观,也用了很多独特的镜头去拍驴,让观众更容易就和这头动物产生共情,被困在车里望向草地上奔跑的马时的羞愧、处在欢呼人群之中的不知所措等;甚至还拍了驴的意识,困境时会对女主人产生回忆、思念。于佩尔段落,其实和被杀的司机、群殴的球迷等等段落一样,不过都是借一路颠沛流离的驴之眼,来看这世界上荒谬的人类。只是电影在驴的行动线上做了大量的省略,稍不留神就很容易搞蒙,驴怎么一会儿在这一会儿在那。第一场戏的视听很棒,更棒的是驴逃走至森林一段,影像观感极佳氛围营造到位,不觉间已与驴的恐惧与迷茫感同身受。当动物与人产生情感后,动物协会再以保护的名义把动物带走,是真的在为动物考虑还是是一种缺乏人道关怀的形式主义?是为了剪彩时一乐?正如片中不断出现的红色一样,痛苦且残酷。
#VIFF2022 廉价的《方形》。看得出来老导演真没油了,这么多议题随便往深一些都能大做文章,但却只能浮光掠影地拍,而且很多视角和这头驴完全无关。哪怕投机取巧成这样,甚至也凑不出90分钟片长,看似包罗万象,实则皮毛都没有。最后,希望所有没啥音乐品味的导演,别再把你的喧嚣配乐塞满整部电影了。
一头具有当代艺术思维的小毛驴的人间历险,目之所及,光怪陆离,喧嚣骚动,世相狰狞,精疲力竭。此情此景我想吟诗一首:如果驴知道,俗世多辛劳。行行重行行,昼夜把命逃。流离又漂泊,何处诉烦恼。不如变朵云,取名叫EO。
这部电影非常非常可怕 我就想起来我看见套圈游戏中的大鹅,大鹅知道被套上就要走了,就要死了,大鹅躲着每一个圈,每一天都是生死循环。
流浪驢的波瀾奇遇記。
#BFI #Newreleases 总感觉这部电影的内核有点儿像《幸福的拉扎罗》,圣徒化的驴子,最后替世人“赎罪”。以驴子的视角俯看众生,人类社会始终是比动物社会残酷的,以这种反差制造的错位感挺有趣,会发现人类更像动物。视觉上构图还蛮喜欢的,低角度仰拍效果很好,动物的POV也很不错,就是很多时候视角切换不是很喜欢,也不喜欢频繁使用的红光,可以理解是用红光对照的是桎梏牢笼,对于驴子是那情感,对于白马那如同旋转木马般的转盘,对于司机是那欲望。听觉上也比较纠结,细腻的环境音太诱人了,但是配乐参与度太高了,破坏了那种自然美感。
大師老矣...了無新意地動物視角切換、樣板NPC人物出場、震耳欲聾喧賓奪主的配樂,最後再來給你一劑「本片絕無動物受到虐待」的絕對政治正確,眼球翻到後座去ㄌ
#Cannes 2022 我的目前为止最佳出现了,画面影像做到了极致…屠宰场的每一个都是自我的投射
类似战马的创作思路,局部的凝视效果其实与去年的Nope当中对奇观的仰望一致,此处人类社会行为化身为奇观,对驴成为一种驯服/归化的展示。然而,子非驴,安知驴之乐。
所以为了补全咱驴这趟冒险的阶级光谱,就请出了于佩尔友情出演?!虽然于阿姨还是比客串老妖Udo Kier圆滑养颜多了,但确是全片唯一脱离咱驴视角的段落,人际关系篡夺高潮的矛盾焦点,顿时打断故事能量,感觉一张舒服的床被大吨位坐塌了一角,必须扣星。另外,摄制团队怎么确保参演驴们的wellbeing呢?尤其是反复重拍、把驴丢进牛群和球迷群时?
小驴😭
视角非常可疑:其一,镜头有时驴子的眼睛,实际又是导演的眼睛,等同于导演将自己的意志加在一头驴身上,因此需要更扎实的技巧,目前显得刻意了;其二,在东亚,我们常用黄牛等动物比喻人劳碌悲苦的一生,这种设计并不新鲜。影片或许尝试折射一个生命在现代社会里的困顿(有动保抗议等经历),视听风格却如此古典,有一种隐隐的错位感。总之,是部很分裂的片子,概念大于实质,最大的亮点是配乐,延展了片子的解读空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