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兰西特派》剧情介绍
《法兰西特派》长篇影评
1 ) 《法兰西特派》纸媒时代的一次优雅谢幕
《法兰西特派》的演员阵容实在让人惊羡,本尼西奥·德尔·托罗、阿德里安·布洛迪、欧文·约翰逊、蒂莫西·柴勒梅德、弗兰西斯·麦克多蒙德、蒂尔达·斯文顿、蕾雅·赛杜……这豪华的影帝、影后卡司让人感慨也只有韦斯·安德森能有如此强大的号召力了。
韦斯·安德森的电影风格一直以童心的视角去讲述成人的故事,无论是电影场景的设计还是剧作风格的展现,他的电影都像一个色彩斑斓带着童趣的成人童话,也难怪如此多的演员都乐于和韦斯·安德森合作,谁不想在这样华丽的电影中怀揣着童心重新审视着这个世界呢?
韦斯安德森有着自己独特的电影风格,固定的画幅和场景,但在同一的场景会同时动态的发生很多平行事件,单一的画面可以承载如此之多的电影信息,让观众享受过载的趣味。
其次安德森也是出名的强迫症,严谨的中轴构图,电影细节的苛刻也让他的电影欣赏起来有着视觉统一的乐趣。
且安德森对色彩的应用也永远是华丽缤纷的,梦幻的质感往往可以打动观众的视觉。
在传统安德森的电影里,在他缔造的这个梦幻光影王国里,往往所讲述的故事却又是落寞和忧伤的。
可能是《天才一族》里对人生的感慨,也可能是《了不起的狐狸爸爸》中的家庭责任和个人梦想的选择,甚至也是《布达佩斯大饭店》中致敬茨威格对那个逝去年代的感伤。
在韦斯安德森的电影里没有绝得的坏人,他用一种近乎于可爱的特质去讲述故事、刻画人生,我们打开一部安德森的电影便是打开一个包装精美的礼盒,而其内核则是敏感且让人难忘的忧伤心绪。
《法兰西特派》同样也是一部典型的韦斯安德森电影,电影虚构了一个曾驻法国的美国报社编辑部,电影独特的用一份报纸的打开形式给大家翻阅了一份叫《法兰西特派》报纸的最后一期。
电影在一开始就告诉观众这个编辑部的一些基础风格,主编是多么宠爱他手下的作家,然而这是他们最后一期了,因为主编离世了。
随后电影就按照几个专栏故事展开来,完全以一份报纸的阅读形式,从游记、艺术专刊、政治专栏、美食专栏以及讣告给观众带来不同风格的故事。
同样这部电影也是韦斯安德森对过往时光的一种缅怀,纸媒盛行的年代,专栏作家的时代。
其中最让人印象深刻的则是艺术家和狱警的故事和专栏记者与革命青年的故事,这两个故事极具代表性的表现一种乡愁般的忧伤。
韦斯安德森的情感催化从来不是直接,而是潜藏在糖果般甜蜜外壳中的,当舌尖触及那一丝对人生的喟叹时,糖果真正的滋味才在口腔里弥漫开。
所以看安德森的电影需要耐心,在浮华的电影表层被剥开后我们才能找到那份慰藉自我的情感种子。
在《法兰西特派》中安德森所建立的人物都是背负着过往的伤痛的异乡人,精神失常的画家、何以为家的女狱警、烂漫纯真却意外死亡的学生等等,他们围绕的核心便是一种逝去的、美好的时光。
像《布达佩斯大饭店》一样,安德森以知识分子的眼光于现今表达了对过往美好的时光惦念,那是充满文学、理想和激情的时光,如今我们在互联网时代,接受着海量的信息,专栏仿佛一个久远的名词慢慢被人遗忘,而安德森则将专栏这一形式和电影结合,重现了那极富个人思想表达的写作年代。
最后一幕的讣告也显得格外伤感,一个时代的落寞,一群人的告别,或许于此浮躁的年代,我们偶尔乡愁发作回望下过往的那些以人为主体的表达,反思下这个信息嘈杂的年代我们是否要慢一些,就像《云上的日子》里的那个故事:“在墨西哥,高人要迁上山顶,请了工人搬运行李,走到某处,工人停下不动,高人大怒,无法叫他们继续,也猜不透为何他们会停下来。
数小时候后,工作再次启程。
最后,领班决定解释原因,他说,他们走得太快,把灵魂丢掉了。
”那么翻开韦斯安德森这份报纸何不关上手机,慢慢的去品味这一个个慢时光中的专栏故事。
2 ) 媒介上的自由
媒介上的自由——《法兰西特派》影评尽量让它听起来像是你故意这样写的。
1、如果《布达佩斯大饭店》讲的是优雅欧洲的逝去,那么紧接着的自然是二战之后那个令人心乱神迷的时代,这个时代在艺术上的两个中心,毋庸置疑是美国和法国。
《法兰西特派》同时致敬着《纽约客》和法国,这一点是显而易见的。
欣赏这个作品也是极其容易的,安德森在画面调度上尽显美国式的余裕,故事本身也不落俗套,更重要的是,只要观众不仅仅带着看娱乐片的心态看这部电影,那么就算我们不做过多的深思,也很容易意识到其中探讨的怀旧因素、媒介因素和至高的主题。
因此,我很乐意写一篇涉嫌“新批评”的分析,也就是把作为整体的作品之许多细部展示出来,而非任由观众自我阐释——当然,我并不能完全保证我解释的正确性,很多细节多有遗漏,敬请原谅——我相信这种自我阐释是易于自发的,所以影评不再仅作为一种诱导手段来吸引更多人严肃地看待这部片子,而更要进入与已经严肃看待这部片子之人的对话中去。
2、自然,入场券是对作品视角的一般分析,安德森非常强烈地试图提醒观众这一点,以至于他直接把画面分成了16:9和4:3两种比例,以及在16:9的长画幅中塞入一大一小两个4:3的画幅。
在第一个故事中,长画幅出现的典型场面是画商看到画家的湿壁画时的状态;第二个故事中,则整个象棋战争都是用长画幅呈现的;第三个故事则似乎并没有长画幅。
这是在电影这一基础性的媒介(A)上做的文章。
余下的媒介,按照其被(A)呈现出来的状态,依顺序有《法兰西特派》最后一期报纸(B),报纸中的五个专栏(C),第〇个专栏《本地特色》-《骑行记者手记》没有表现出第四层,第一个专栏《艺术与艺术家》-《水泥杰作》是作者的一个演讲(D);《政治还是诗歌》-《宣言的修正》是作者的报道,所以也没有表现出第四层;《味觉与嗅觉》-《警察局局长的私人餐厅》是一个采访(D),还有最后的讣告,也很难说表现出了第四层。
这些报道的内容本身和报道不是同级的,因为就算以一个采访而言,我们也是看到采访又听到内容,所以普遍存在一个媒介(E),它在日常生活中不明显,但被电影良好的转导出来,值得注意的是,每在(E)中增加一个叙事者,它就会增加一层(E),如女记者记录的故事中,男主角作为一个视角讲述的故事就和女记者的故事不在同一层,但它们却是同质的,尤其是女记者本身参与了她叙述的事情,所以我们暂且把这类媒介算作(E’)。
在叙事内容(E)中,第一个的故事里面有绘画、PPT等媒介,但它们并没有充盈整个屏幕,所以只作为(E)的一个内部组成部分,第二故事里面则用戏剧(F)表现了男主的一些引述,第三个故事则运用了漫画(F)来表现所有追逐动作戏。
除了这些媒介上的提示,电影的颜色也说明了一些与视角相关的东西,黑白是大部分叙事的主要颜色,但也有不少彩色出现。
于是,现在的基本问题就是如何把画幅-媒介-色彩和叙事内容对应上。
我相信这得一个个分析。
第一个故事《水泥杰作》讲述一个监狱中的画家如何通过其极其抽象的绘画方式征服世界。
这篇报道(C)呈现为演讲(D),让我们且将其假设为D作者(α),占领全知视角(这个视角是文章写作的视角,不是电影镜头的视角,实际上该作的电影视角几乎一直都是第三人称观众视角,改变的视角则和文章写作视角的改变有关,为了不写的太乱,我们就不重复分析了;同理,叙事这个词也主要指文章写作时在叙事-介绍,而不是在描写,这是本文的一个基本区分),也是主要叙事者。
当她成为其叙事之中的角色时,我们将其称之为E作者(β)。
与它同级的其他角色包括画家、狱警、画商等(β),到此为止。
剧情很简单,但同时很精彩,我们很期待画如何被呈现出来,也很期待画家的结局,画家本身的形象也并非铁板一块,带有神秘的丰富性。
但让它真正变得有趣的,还是通过电影画面来展现各个角色(β)如何与画家(β)和它的画相遇。
长画幅和叙事之间的关系很明显,第一次那是8幅画刚开始被展示出来时(0:36:05)。
值得注意的是,那时候E作者(β)也正站在画面前。
在这之外的都是D作者(α)的叙事,这时候她就算亲历了进入监狱的过程,但她毕竟并没有用E作者(β)的第一人称视角来写,而画商和警察对话等情节,她就更没有亲历,因此都是短画幅,该故事结尾处的长画幅也可以这么解释;颜色出现三次,都是对着画和作画(β)的,但我们不能简单地认为它说明流传至报纸(B)发布时还能在这一层看到就是彩色的。
仔细观察,在进入(E)层后,如果报道存在对物件的描写,但字幕没有念出这些描写,反而用一个电影画面替代时,它才会是彩色的。
换言之,彩色代表了第一人称电影画面对第三人称文章描述的替代。
这在第一个故事中最为明显,因为画总是难以用文字描述却可以直接被电影屏幕呈现。
而在(E)之前,报道(D)是彩色的,因为它D作者(α)并没有在(D)中描述自己,反而凭借电影画面在场于观众面前。
如此我们就说明了三者在第一个作品中的联系。
总结一下,长短画幅重点在人称,而彩色与否的重点在替代。
带着它,我们进入非常复杂的第二个故事。
它讲述一个记者如何卷入某个青年革命家的短暂人生之中。
当然,作品规避了具体的政治问题,如《宣言》的具体内容都会被旁白压过去(1:00:16就是一例),最后甚至用电信号短路来涂掉那些条例。
不过,作品也没有落入革命者形象的俗套,即要不然是伟光正的,要不然是纯粹滑稽反讽的(比如《大独裁者》),相反,甜茶虽然是一个装大人的孩子(尤其是那幅装扮),但是他也带着坚韧、智慧、浪漫等复杂性格,且其终局也并不十足滑稽,相反还带着一丝落寞,有点类似《布达佩斯大饭店》里的古斯塔夫。
说回对应关系,这里的要紧之处有两个,其一是D作者(α)和E作者(β)并没有界限,报道用的就是第一人称、直接引语,作者也确实加入了那场革命;其二是出现了和E作者(β)同级的叙事者男主角(β),作品展示了他的视角,而不仅仅是用E作者(β)来代替之。
在第一个故事中,画家并没有做任何回忆,换言之,电影表现出来的画家和他的缪斯之对白可以是D作者(α)编造出来的,从而取消其画家-缪斯(β)主视角以及现在进行时的特性。
但是在这个故事中,D和E之间没有区分,所以作者并不是全知叙事人,她因此需要引述男主角(β)的话和内容,这就包括男主角(β)的隐私生活以及过往历史。
这些内容都是彩色、短画幅的,而且运用了戏剧表演的形式呈现出来,其效果非常震撼,颇有布莱希特之神韵,比如0:56:25分戏剧角色不断强调一句话,使得这段戏剧和在其之上的电影“正常”叙事手法之间产生明显的间离,大家都知道这段并没有模仿现实,这反而展现出戏剧的特殊性,从而把那个跳楼男孩宁愿自杀也不愿意回归肮脏的大人社会之事深深映入我们的脑海。
不过,我们还需要进一步区分,男主角(β)的叙事是(E’),而(E’)之中有F,它们都是彩色的,所以以戏剧形式作为媒介来区分,此中出现的角色是米奇、男主等(γ);而(E’)男主(β)和E作者(β)不同级却同质,所以用颜色区分。
颜色区分同时也符合第一个故事中总结的条例,即文章的描述式写法碍于作者的非全知视角而不能够亲历男主角讲述的故事的现场,而男主角如果要讲这些场景给作者,那么他也没有进行第一人称和描述。
彩色画面的叙事者其实是男主角(β)和米奇(γ),他们当时都在他们描述之地的现场,但他们如果在报道中说话,那么它不是直接描述而是间接的叙述,所以它被替代为电影画面。
这说明彩色依然代表了第一人称电影画面对第三人称文章描述的替代。
再说画幅,长画幅几乎占据了所有主要叙事,显然,只要是E作者(β)在场作为亲历者第一人称的就是长画幅,不在场作为第三人称的就是短画幅。
拿作品最后男主角(β)修电塔落水而亡那段来做个分析(1:06:41):它最开始是黑白短画幅的,因为它是D作者(α)的视角,却不是E作者(β)的视角,那时候女主显然并不在场。
正接着,它突然切出了几个彩色短画幅画面,是很多人在听他的广播。
切回黑白短画幅,突然切成彩色短画幅(1:07:46),男主角被闪电劈中,(切出几个黑白短画幅的闪电劈中时的全景画面,但这里不适宜带入分析,因为它很明显在模拟闪电闪烁时分不清颜色的视觉效果,所以根本不知道它属于黑白还是彩色,毋宁说这是安德森对彩色问题的自觉调侃和提醒,我觉得闪电的戏剧感也可以这么解释),之后的彩色画面则是对男主身后之事的展示。
因为这些都是事后的报道,所以女主不在场,作为第三人称发言,一直是短画幅。
彩色画面则是E作者(β)的真实所想、所看,她看到了男主角死后社会上的各种追思,以及咖啡馆的现状。
再加上此时的旁白却还是第三人称式的叙事,而非对追思、咖啡馆的具体描述,所以它是彩色的,它以电影的直接呈现替代了本应该由报道完成的描述性内容。
直到最后(1:08:53),我们看到一个黑白短画幅的E作者(β)躺在床上戴着防毒面具的画面,一开始,防毒面具是为了防止被催泪瓦斯伤害戴上的,但随着男主死去革命结束,一切看起来都没有变化,此时清新的空气反而看起来是有毒的。
寓意明显,但这里看起来有些诡异,因为E作者(β)正在现场,画面却是短画幅,展示的是一个场景,但颜色却是黑白的。
不过,我们的分析依然完全正确(在长画幅出现之前大多也用的短黑白画幅,解释是相同的),一些虚假的错位反而更进一步展示了它的有效:这个时候,叙事者显然是D作者(α),旁白正第三人称地念诵着她的报道,所以短画幅没有任何问题,这个报道本身就是在写她自己,且正因为在写她自己,所以不可能是E作者(β)在说话(注意旁白念了一个日期,这也是提醒);也正因为此时的视角是D作者(α)的,E作者(β)的主视角被剥夺变成一个纯粹的角色,D作者(α)在旁白里做的的是描述,而且这个描述并不是其房间的描述,所以它就和画家-缪斯(β)在第一个故事中一样是黑白的。
第三个故事也很简单,讲一个厨子如何帮助警察拯救自己的孩子。
此时的D作者(α)在一个访谈(D)上,整个作品大部分时间都是短画幅黑白画面,我们现在已经基本可以把它转述为,这是E作者(β)在进行第三人称叙事。
出现的第一个彩色画面是警察局长邀请E作者(β)吃饭时的饭桌特写,这时候显然应该有一个描述,所以它变成了彩色,但是作品的旁白依然在进行第三人称的介绍和叙事,所以是短画幅。
第二个(1:26:07)是小孩儿(β)看见绑架他的女人(β)的眼睛时的画面,这时候的主视角只能是这个男孩(β),因为其他人根本就不知道这件事,所以彩色画面是属于E’的内容,从而和第二个故事男主角(β)讲述咖啡馆里的故事一样是彩色短幅,第三个厨师上楼梯的镜头也同理。
值得注意的还有一个对D和E之间差别的提醒,就是采访(D)的过程中,D作者(α)和采访者(α)谈起自己过往经历的时候突然从彩色变成了黑色,这时候其实作者就已经变成E作者(β),进入E层的叙事空间了,在念诵他之前写的其他文章了。
只不过这个E层和前一个故事并非同一个,所以它也不同于E中的E’等,最好把它编为E1。
至于作品中出现的动画画面,他照理应该是通过(β)级角色叙述(γ)角色的事情时出现。
单在这里展现的并不够明显,即动画究竟是谁的视角,尤其是最后的追逐戏,没有旁白,所有人都在场。
所以我们或许可以把这个新媒介的运用理解成:说明除了E作者以外的(β)级角色应该详尽描述但没有的情节,比如偷人和追车。
此时旁白不是(β)级角色,而画面如果被转译成文章就会极富有描述性。
带回第二故事出现的戏剧,确实也是男主角(β)叙述的米奇(γ)的故事,但没有出现男主角(β)的旁白,只有米奇(γ)现身说法。
与其他专栏不同,该作在结尾之前就切回了报纸B这层,讲述C法兰西特派老板和C作者要求改稿的事情,老板看向废稿,于是立即进入E作者(β)的叙事,我们看到一位可敬的厨子,对新鲜的味道充满好奇,勇敢,谦虚,但也并不完全是正面的,因为它带有极端性和危险性。
这样的角色作为外来人的形象,其实在说明伟大的记者都是这样的人,他们虽然应该保持记者的中立性,但他们会为了自己热爱的报道对象挺身而出,会为这个世界不断发生的新鲜而危险的事情而兴奋,他们虽然囿于生计有时候不得不推迟自己的出发和探索,但他们敏感和勇敢的心灵永远在新鲜地搏动。
这一层都是黑白短画幅,符合第三人称、叙事这两个特点。
说完这些D以下的部分,还剩下骑车日记和讣告,骑车日记非常简单不再赘述(其中有一段0:07:07和黑白相关,一个大画幅里同时出现了黑白和彩色。
由于和过去-未来有一定的关联,这里就像是第二段里的闪电一样,看起来更像是严格对应之外为了视觉效果而做的诡计),讣告作为C层,它分为彩色的C层和黑白的D-E层的,前者说的是老板一般现在时的生活,包括他和其他C层作者的互动。
这也可以从第三部分老板第一次出现时因为属于E作者(β)的叙事视角所以是黑色的看出来。
至于黑白D-E层自不必说,讲的是具体的下葬等相关过程。
作品结尾处是彩色的,它实际上正处于C层,和老板与各个作家对谈处于同一水平。
以上就是我对媒介-画幅-颜色与故事之间关系的分析。
我们已经可以开始赞叹安德森用如此方式极其侧面但是丰富地展示出来的《法兰西特派》之性格、老板之性格以及无聊镇的性格。
这里不再赘述。
下面我想谈论一下第一人称-第三人称,也就是长短画幅的事情,以及叙事-描述,也就是颜色的事情。
3、先说后者,叙事和描述能够同时在一部文学作品中出现。
但我们很容易有这种感觉,就是无法通过作者的描述清晰地看到作者描绘的场景。
如果大家看过一些密室类侦探小说而小说却没有给出平面图,那才真是杀人般的痛苦——《本阵杀人事件》的密室我就只能目瞪口呆地听他讲,几乎完全无法想象。
这是文字媒介的固有问题——它通过取消和读者的实时互动来换取长距离、长时间的信息传递。
在古希腊,文字还没有诞生时人们都是通过对话来传递信息,此时如果描述难以传递足够的信息,人们可以通过画图、指手画脚甚至实指来予以补充。
换言之,言语是活生生的,但文字取消了这种互动性以换取更多人的阅读。
这么做自不能简单地看做某种毒药,即通过书写,我们遗忘了一种活生生的知识-状态而只能通过再阅读来激起死知识。
同时,它其实锻炼了一种更细致观察世界来描写以及运用更有效语词来描写的方法,大量的语词得以被发明:它们处于一大段叙事中间,因此就算这个名字是陌生的,但通过代入这个场景,我们就逐渐知道了这个词是什么,而不通过图画和实指。
比如“榫卯”就可以在描述的簇中获取其意义。
这种描述的最高境界就是诗歌,它甚至反转了对象和语词的关系:“一团温暖的火”本身就可以为我们带来一幅完全不同的世界图景。
不过这种局面随着打印机-电影-电视等富含图画三个步骤而逐渐改变:当描述较为困难时,我们会选择在旁边配图而非仔细描写,它显然更容易达到实用目的,到后来,描述反而成为了辅助,图片本身行叙事-介绍-描述的功能。
它也同时是好药和坏药,坏的成分毋庸置疑,就是许多语词的衰落。
当作者难以描述氛围、场景、对象时,他大可以转行做导演。
在这个意义上,格里耶和新小说派反而成了对电影等图画媒介的对抗,他坚持通过书写来展示极其难以展示的日常事物,如一扇门,一个街角等上手者,把它们置于在手静观的位置,从而产生陌生化效果。
好的则正如这部片子所展示的,它成为一种高传播性的混合媒介,从而可以在不同层次上展示各种媒介并传播各地。
这一点随着网络实时分析而衰落,后者是信息传递速率的最便捷模式,即一种可暂停、可远距离传输的对话模式。
它使得新发明语词的需要越来越少,因为我们可以让对方直接看到我们的指示内容。
此时,电影反而成了怀旧之物,传递内容过于低效,有时候还意味不明。
不过,正因为意味不明,它便具有大量重复阐释的空间,这在对话和实时分析里是没有的,读过柏拉图对话录(比如《斐德若篇》)的人都能看出来,与话者如果没有看懂,那么他就会要求谈话人说的清楚一点,甚至要求苏格拉底现场朗诵一篇优美的诗赋,此时,信息汲取者不重复,因此也就缺乏反思性,其具体表现就是要求一切媒介最终都归于实时分析,而实时分析需要不断磨合传输时间和处理时间之差异,这使得其采样频率越来越高,很快就超过了人对世界的知觉间隔到达DSP,甚至使人都变成了系统中被采样压缩处理的信息。
这时候的人却不想着反对它,而是要求其他人也顺乎它:立即提供信息,立即提供解释,立即满足与话人。
而《法兰西特派》对此进行了极其反讽的处理:首先就故事来说,三个故事就叙事而言都简单的离谱,符合一个报纸所需要的简单、惊奇、有趣也不复杂的需求,没有处理的负担。
但观众如果不去关注那些“尽量让它听起来像是你故意这样写的”画面,他很快就会因为画面的繁复和离奇而迷失方向,甚至眩晕难受。
1小时43分钟的作品其实提供了很多很多的信息,它们同时掩藏在信息溢出的字幕、极其复杂的构图以及各种切镜里,前文第一部分已经展示了一些——尽管本文没有分析多少旁白的话语之分量,不过相信二三部分那些颇具文艺气息的话语会打动某些人,但也会因为它是《法兰西特派》报纸内容之“真实”反映而得到不那么喜欢文艺话语之人的原谅——但只关注故事的人却会觉得它空泛无物难以忍受。
如果这些人不是眼观六路还通晓历史,那我只能认为他们根本没有处理这些信息,任它们被过滤,然后希求在豆瓣的影评里得到实时的疑惑解答。
这其中没有折返,没有再度品味,观众通过不断接受新信息来解决以往通过反思来完成的事情,虽说就知识而言事情得到了解决,但是就一种主体的锻炼来说,人只会越来越痴呆愚笨,缺乏实践。
更有趣的是在画面处理上。
前文讨论的是要表达一个信息时的媒介情况,现在我们说一个媒介蕴含的信息情况。
按理来说,一句话里的信息是较为清晰和明确的,所以我们对话语信息的处理也是容易的,交往中的肢体语言甚至更为清晰。
但一个画面的信息是极端多重的,当里面缺乏指示之时我们只能根据自己的意志去处理。
安德森当然给予了指示,然而它们本身就内嵌在各种画面之内和之上,因此本身还需要处理,以至于就算电影只想让观众暂时放下心思关注一幅画,如果观众没有对指示有一个安心的理解,他也只会感到疑惑(1:22:47出现的书籍就是典型例子)。
更讽刺的是,描述本身是缺乏直接给出的信息的,它的目的是展示画面,再由读者提取信息,电影画面取代描述,其实为观众的信息处理减负了,观众在面对彩色画面时却很容易不知所措,根本不提取这些信息。
这同样暴露出各个媒介之间不分优劣的不同。
一篇纽约客的小说写很多倒叙、插叙、间接引语、直接引语是极其正常的,观众也会自觉带入。
这时候它的信息处理显然具有优越性;电影试图仿照这些视角转换,却导致画面信息越发复杂难解以至于需要破译,这展示出电影媒介在信息处理某些方面的短路:摄影机镜头其实预设了第三人称的观察视角,必须要有提示才会进行转换,正因为需要提示,它不能完全按照把镜头后方的人和叙事主视角对齐的方式来完成,否则它就很难找到区别,还会陷入非全知视角的麻烦里。
此时,文字中的叙事是自由跳跃的,受束缚的反而是作为新媒介的电影。
安德森在此处刻意选择了电影最难表现的内容予以展示,并且展示的赏心悦目颇具绘画、设计美,而且展示方法也具有规律性,因此发难者也很难说这是随意的,只不过是艺术家的碰运气行为。
这种认同最终上升为对信息传输效率的批判,要求所有观众去自由地、随心所欲地感受各种媒介。
前文提及有些片段的颜色、画幅没有办法直接对应于媒介、视角,比如闪电那里的黑白和戏剧感,或者第二个专栏最后女主坐在床上的场景。
通过它们,我们才会脱离一种与电影和文章的简单诠释关系,意识到它们作为媒介的媒介性。
且正是在这种对比之中升起了一个超越任何前述媒介的“无所介”之介,在那里我们才可以随意选择进入任何媒介,此“乘天地之正,而御六气之辩,以游无穷者”由比较而被发现和把握,我们借此才能进入真正的“游戏”之中,此游戏与其说是现在的电子游戏(这个可能需要更进一步的讨论),更像是安德森对电影所做的事,也就是所谓玩电影,从而让电影既是电影又不是电影,从而进入一种无意之有意中。
4、“花开两朵,各表一枝。
”让我们在对“道理”做进一步阐释之前先讨论一下黑白画面的人称问题。
这一讨论是文学理论中非常经典的,它事关不可靠叙事人这一概念。
侦探小说里有所谓叙事性诡计,通过混淆叙事人的身份来掩盖某些破案线索,但身份的不同毕竟会导致叙事时的区别,破案的真正线索反而就来自于此(典型代表:《剪刀男》,别担心剧透,它就是打着我在叙诡的旗号出来的)。
经典文学里芥川龙之介的《地狱变》,石黑一雄也甚是沉迷于此。
简单来说,当叙事主视角本身参与了故事的进程,而且在行文过程中表现出了情绪,那么它就是不可靠的,其极端状态是写一本讲一个人在写小说的故事,它通过双重套娃完成了“元叙事”。
在《法兰西特派》中,最后一个专栏《警察局局长的私人餐厅》(这名字有点奈保尔),它本身就完全可以当作小说来看,就算这里也有不可靠叙事问题,因为它是冒险小说,且不关涉事实而不重要。
但第一二个专栏都具有新闻采访(人物;实地)的性质,所以叙事的可靠与否成为了作品能否立住的关键。
第二个专栏甚至专门提及了“她应该保持作为记者的中立性。
”(1:01:21)。
此时,第一个故事里几乎都是短画幅,第二故事里的象棋战争则全是长画幅,它说明对对象的展示和对历史的展示之基本不同。
简单来说,如果一个演讲稿要展示的重点是一个对象,那么我们期待的是对这个对象的“知识”之概览,此时,真事和假事都是读者所需要的,它们共同形成读者对对象的认识的一部分。
“画家的画是瞎画的,画是被炒作的”这个句子可能是假的,但是它是对画家的一种确实存在的评价,那么把它展示出来就没有什么问题。
“真”不构成对事物的认识的必要或充分条件,所以第一个作品中才会出现大量的假想对话以及过于传奇的故事。
可是,作品的叙事反而是第三人称,也就是所谓客观-上帝视角的。
它以介绍概览为由免除了这种视角的伦理责任,反过来也强调了客观视角并不具有客观性,它是在“概览”或者其他目的的引导下所做的筛选。
而一个采访要展示的重点是历史(无论是对象的历史还是事件)时,“真”似乎成为了最为重要的部分,否则所有的再现都是臆造的,不能让读者确实获得这段历史的知识。
“真”成为了必要条件。
但如何才能达到真呢?
我们看到第二个作品里E作者(β)和男主角(β)甚至有肉体关系,她又如何公正地展示这场革命运动呢?
这是一个客观视角遭到怀疑的时刻,其解决方法则是真实地表露自己的一切行动,把自己纳入自己所写的故事之中,承认自己是一个不可靠叙事者,那么其不可靠性就是可靠的。
换言之,历史叙事可能是假的,但是人们意欲表现这样的历史叙事,却是真的。
读者因此可以透过这样的写作考察出写作者的心情,这种写作时的心情是毋庸置疑的。
在作品里,这就是E作者(β)对男主角(β)的爱护,对革命的期望和失望以及对新闻工作者身份的挣扎。
由此,一个重要话题:表现和再现便出现了。
如果一切历史叙事被当作对历史的再现,那么海登.怀特等人的怀疑就说得过去:我们没法确定书写者不是另有目的,所以我们首先需要考察这个文本的文学结构,再看看能不能通过它渗透入历史空间。
此时我们很容易走入怀疑主义的极端之中。
但如果我们把历史叙事看成作者对此事的表现从而更关注他对此事的情绪状态,那么这种情绪本身是真实的,因而可以完成一种情绪史的书写。
反过来,真正伟大的书写绝不能仅仅是再现一个看起来真实的人物或事件,而是让作者的心思流淌于字里行间。
此时,不可靠的叙事作为限制,才能让作者随心所欲地表达,从而真正呈现出某种东西。
我们都知道,《法兰西特派》致敬的是《纽约客》,一如《布达佩斯大饭店》致敬的是茨威格,但这里面的虚构简直都没有欲盖就弥彰了。
我们还知道,第一个故事致敬的是美国的纽约画派,是抽象表现艺术的一支,其代表人物和画作是波洛克的滴画、罗斯科的颜色画和库宁的《女人》系列(0:27:43把这三位的画法都过了一遍),对这段历史比较了解的应该尤其能把库宁和画家联系在一起,各种线索是明显的;第二个故事讲的是20世纪后半叶西方世界最著名的事件之一,五月的法国,街垒和学生,《戏梦巴黎》,《肯定那种决裂》。
无数哲学家倒在这里,又有无数哲学家从这里走出来;第三个故事我不了解,不过考虑到前两个故事都有明显的历史性,第三个或许也有吧。
不管怎么说,我们几乎可以把这三份专栏当作历史上一些真实专栏的戏仿。
它们可能是蹩脚的、伪造的、拙劣的,但更新后的戏仿之作却不断激发出浓烈的怀旧情绪和浪漫思虑,这样的状态是无可置疑的。
它是在毫无限制之情况下的自由抒发,它表现它本身,而不是隔着其他东西再现,所以它的随心所欲成为了它的真实之证明。
此时,历史考证可以为这部作品增光添彩,却不必是欣赏这部作品的必要储备。
5、两个部分的分析都指向了“如何获得自由”这一问题,而《法兰西特派》所反映的年代,正是今日的我们所认为的最自由的年代。
虽然说今日的我们有近乎无数的渠道来表达自己的想法,可事实上我们总是考虑着金钱利益等等:新闻越来越求快而不是求真,这实际上提供了更大的束缚,在以前,就算有记者行为道德准则,也有些人可以为各种理由来做些歪曲,但近日,不快的新闻没有办法遭到关注,因此在新闻业内部就会直接被筛除根本难以见报。
这样的事情在这样一个光速时代甚至有些屡见不鲜以至于人们都发明了不少借口来掩盖自己的身不由己。
《法兰西特派》一开头就强调,老板小亚瑟.豪威泽对财务、插画等人很严厉,对自己的记者-作家却非常宽容,就算版面超了、写作重复、无理报销、主题偏移,他还是会刊登,在讨论如何修改文本时,他也非常尊重作家本人的意见。
正由于如此宽松的基础环境(它似乎可以和报纸B挂钩,在其上发生的事情则是C),各个作家才能够不受阻碍地表达自己的意见。
再看各个专栏,第〇个,骑车日记,本身就散漫异常;第一个讲述抽象表现画派的故事,它在美术史上享有很大的声誉,因为它让绘画彻底没有了任何限制,同时仍保留着“美感”。
如果说20世纪绘画一直是抽象的,那么它作为第一个声名鹊起的美国画派与立体主义、野兽派、未来主义、超现实主义以及康定斯基为代表的抽象派有着明显的区别。
后者诸君除了康定斯基甚至没有放弃对一个已有对象的呈现,虽然马蒂斯意图用线条展示情绪,从而让表现式的精神力量进入绘画,超现实主义如马格利特也更强调具象的对象背后的神秘感觉,但只有康定斯基彻底放弃了对任何对象的摹仿(试看《黄.红.蓝》,下图),仅仅就线条本身来抒情,并提供巨大的解读空间。
康定斯基《黄.红.蓝》此时,似乎没有任何限制作家的地方了,除了这块画板,因为去掉画板本身,画就仿佛不再是画了。
然而,库宁、波洛克等人却超越了这一极限,把画板至高无上的位置拖入了绘画之中。
看过波洛克用扫帚奋力地刷画以及库宁那困难的笔法时,我们就会明白,这些作品的基础并不是画板,而是画家和画板的搏斗痕迹,也就是一般的物理空间,由此绘画达到了形式化的巅峰(比如库宁的《女人一号》,下图)。
不过,正如《法兰西特派》所说明的,我们很难确保里面没有任何炒作的成分,就算库宁也一如故事中的画家也可以画非常好的立体主义以及写实画。
不过,那时候的人们并不介意这种炒作,因为一种新观念和新技法确实流传了开来,钱不过是一些小小的代价;第二个故事所致敬的历史事实更不必多说,许多思想家甚至将其称为二战之后西方世界唯一有所成效的革命。
它划时代的意义在于它的无所追求。
既往的运动或多或少有着现实的目的和最终的伟大目标的二分。
但小资产阶级的学生们开始走出校园时,他们的要求却近乎无理取闹,根本不可能实现。
我们简直可以说,他们并不想有所建构和满足。
此时,抗议活动呈现出的是它的模糊面貌。
哈贝马斯在去美国之后,曾经试图在其法律理论里设计一些法律法规来专门用以管理暴动,获取其所欲来商谈与修改,但五月展示了这最柔软规训的破坏方法,那就是无所顾忌,甚至这些宣言的具体内容都是滑稽不重要的(这可以作为第二故事为什么挡掉宣言内容的另一种解释)。
库宁《女人一号》由是,在代表社会的活动(这里还有各种侧面暗示,不再举例)和代表个人的艺术层面(除了绘画当然还有电影技法上的致敬,亦不赘述),60年代都在努力展现一种汹涌的搏斗姿态以摆脱那最基础最柔软的规定。
而它们的见证者和传播者就是无数的纸质媒介。
当时电视已经开始进入千家万户,报纸对新闻速度的追求逐渐无力,因而转为有质量的报道。
汉娜.阿伦特的《艾希曼在耶路撒冷》作为极其重要的政治哲学和伦理学作品,其实就是《纽约客》派她去耶路撒冷地方法院考察后写的。
也正因为报纸的原初功能逐渐丧失,记者的写作越发自由,小说版面、书评版面也在增加。
可以说,那是一个彻底的反抗时代,是优雅欧洲逝去之后,人们对自己所在的社会基础的彻底拒绝。
任何事物都值得怀疑,这反而让主体越发严肃和认真。
无所——不是无可——依凭,才能有动力和可能去正视所有东西,从而不仅仅待在无所依凭之依上,而是游走于各个领域,不断探索,不断创造。
这么说,人们难免会觉得有所夸大,再加上这个时代在今日的反思中有一个极其恶劣的名字,我们难道不会怀疑以上的言说吗?
如果真的是怀疑而不是断然拒绝,那是非常好的。
但正因为今天我们又重新找到了某种媒介来依凭自己,无所依凭作为一种依凭,也就被遮蔽了,我们在此地此刻的媒介(流媒体、微信朋友圈、豆瓣APP)上去看那时,自然会觉得那是恶劣的混乱,是投机者的天堂,等等。
第三个专栏就显出了征兆:警察局长当然是权力的代表,他在警察局里发明饕餮,还让警员做服务生;他把孩子一手带大,试图把他培养成新的掌权者。
抢走孩子的人则更像是第二个故事中的反抗者,可他们也沦落到为了一些个人目的。
最终,反抗者死去,孩子重新回到去往警察局长的正轨上他一生中看到的唯一色彩是那个绑架他的姑娘眼里的蓝色——她为了不让他害怕还唱起了一首法国民谣。
救了孩子的英雄因为吃了胡萝卜差点被毒死,我们可以说这让他品味到了新鲜的滋味,可这并不完全是他自愿的,他说:“我只是没有那种兴致让大家失望(1:39:45)。
” 这句话昭示着随心所欲的结束,社会关系再次巩固起来,人们在别人目光的“鼓励”之下被迫做出各种看似英雄的行动(韩炳哲不断讨论的“功绩社会”便是如此,虽然他的讨论总是那么浅入浅出一如他批判的光速时代)。
如今,舍生取义已经得不到大家的关注了,对它的报道是另一个浪漫时代才有的。
三个故事串联起来,便是二战之后(《布达佩斯大饭店》的结尾),纽约画派崛起(中等层面)代表的对抛弃一切媒介的绝对自由之追求,到这种追求在五月(全社会层面)被推向高潮,并于一件警察局小事(个人层面)中走向末路。
自由之欲望减退,《法兰西特派》也就停刊了。
我们很容易这样总结,说这部作品通过纸媒时代的衰落,唱出了一首自由时代的挽歌,从而将韦斯.安德森的作品限制在美学领域,再谈谈他的个人对称美学风尚,便小资产阶级式地消费完这部作品,继续自己庸碌的生活,把刚刚看的电影当作难得的一口新鲜空气。
但只为了展现个人美学的作品是恶劣的,它名为个人,却必然要依附于作者的名声、资本的宣传以及粉丝的热情(这里可以列出不少导演的名字)。
就画面单独来说,韦斯.安德森之作除了严格的对称性,还有静止性、层级性,并最终有一种强烈的结构性,从而突出一到两个角色。
这样,每个在场的物件都要被严格调动来达到画面的平衡。
就算不引用全景敞视监狱,我们也能明显感受到这是一种作者权力的暴露。
所有事情都归属于既有的目的,这个目的却不能在被表现的事情中得到合理的解释,需要借助安德森的地位、其他作品等等。
如果说作者意欲呈现的是一种不拘的游戏态度,即完全随心所欲地展示自己的风格,那么这种自由要不然无以传达出来,要不然因为获得了媒介的支持而压迫了其他于此媒介上的自由人——至少是在观看时。
不过反过来,我们也需要意识到,作者必须依凭什么才能够把无所依的自由之追求和衰落的历史呈现出来。
所以,在依然需要有所依的时代,我们能做的不仅是个人层面的“泰然任之”和“游戏”,而更要极度地黏附于一种媒介,发挥它的最大可能性(虽然在这部片子里音乐似乎并没有特别重要),从而在媒介的使用上获得一定的“正统性”和对这种正统性的偏移,它体现为一个美国人拍法国、一个电影如此纸质化、一个个情节互相关系淡薄又过于复杂。
这样,我们就获得了对无媒介之自由的理解、对自由时代衰落的哀婉,但也有对电影作为媒介本身的怀疑。
安德森同时做到了“道理”的传递以及对“道理”依附媒介的破坏,对电影的本体论-形式化的探索(由此电影的媒介性遭到怀疑)以及对某个具体道理的阐发(它摆脱了媒介的约束),从而让观众愿意获得这份知识,却也不忘怀疑精神。
这才是真正的游戏态度,它拒绝让游戏变为规则的执行,“尽量让它听起来像是你故意这样写的”,当不自然本身是被设计出来的,它也就变得自然而然了。
但能够与此同时传递信息,显然需要这故意写的东西本身是符合所谓主流(比如我们都喜欢对称美)状态的,这样,其故意性才让主流状态成为与自己的对比,从而展示出自然的主流状态之非自然性。
作品的三个故事都是与媒介搏斗的故事,而在媒介A,也就是电影层面,韦斯.安德森也在思考如何利用电影来摆脱电影的束缚,那么,A就是最基础的媒介了吗?
在对这个问题的思考中,自由时代便不只是挽歌,怀旧之后,我们从这些历史沉积中获得的,是新的自由之希望,它是“世界存在的和谐-行星式的本质现身,将在‘无目的的时间’的游戏空间中,既不显现为悲剧,也不显现为喜剧,而是显现为‘开放的世界’。
””所以,no crying,我们还没远远没有到需要哭的时候。
参考文献:[1](德)马丁.海德格尔著.面向思的事情[M] .北京:商务印书馆出版社.2014[2](德)费里德里希.A.基特勒著.实体之夜[M] .上海:上海科学院出版社.2019[3](法)贝尔纳.斯蒂格勒著.意外地哲学思考[M] .上海:上海科学院出版社.2018[4](法)科斯塔斯.阿克塞洛斯著.未来思想导论[M] .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20[5](荷)安克施密特著.历史表现中的意义、真理和指称[M] .南京:译林出版社.2015.[6](美)海登.怀特著.叙事的虚构性[M] .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19[7](美)唐.伊德著.技术与生活世界[M]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2[8](美)费雷德.I.德雷斯克著.知识与信息流[M] .北京:商务印书馆出版社.2021[9](美)埃里克.坎德尔著.为什么你看不懂抽象画?
[M].天津:天津科学技术出版社.2021
3 ) 一些印象深刻的隐喻
1. Owen Wilson站在一个大坑前介绍说这里曾经是一个有名的建筑。
影射了巴黎的Les Halles中央农贸市场,奥斯曼男爵巴黎改造计划的重要项目,建于1857年的大型钢结构建筑群,最终在1973年被拆除,由于土地利用方案悬而未决,现场遗留一个大深坑长达7年之久。
著名的Les Halles之坑2. 男女生宿舍问题的争议引发学生运动。
影射了1968年3月22日巴黎近郊楠泰尔学院爆发的学生运动,其诉求除了反帝国主义反资本主义之外还包括了争取男生自由出入女生宿舍楼的权利。
这场运动是法国1968年五月风暴的导火索之一。
3. 学生运动中一直下国际象棋。
影射了1842年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巴黎摄政咖啡馆首次会面,而这座咖啡馆是当时欧洲首屈一指的国际象棋爱好者聚集地。
马克思和恩格斯在摄政咖啡馆下棋(电影《青年马克思》)4. Tik Tak明显是在讽刺抖音了。
4. 厨师的造型模仿了巴黎黄金时代著名的日裔画家藤田嗣治。
藤田嗣治其他的等再刷几遍之后再慢慢回忆吧。
4 ) 对称的不对称性
也许是因为职业和专业背景,我特别喜欢有趣的叙事方式,“强迫症”式的形式与结构。
好像权力的运作也特别钟爱这种完美主义的表达,对称可能不仅仅因为它美,还因为它权威、高效。
人的关系是否只是权力的关系?
人是否只是规训的产物?
普世价值是否存在?
在今天的社会状态下这些问题貌似更有价值。
电影里所有的人物都有着明确的权力关系设定,老板与员工、不同分工的同僚、父子(女)、老师与学生、警察与罪犯、画廊与艺术家……但是电影仿佛想摆脱、超越这些设定,这些权力关系通过人类社会独有的城市、艺术、美食,甚至童真的政治宣言、暴乱而消解了,当然还配合着美轮美奂的电影技法,不同年龄、性别、种族、职业身份的人(权力主体)可以平等的在同一张床、餐桌、办公室里交流、互助、理解,甚至“好人”和“坏人”都被描述的很可爱。
电影最终都在描述“爱”,它与权力无关,这应该是普世价值的意义,大家本不应该是敌人,因为我们有着共同的目的。
我忽然想起了同样“强迫症”的《去年在马里昂巴德》,正是那种“没有意义”的不断重复、闪回跳跃,解构了庸俗的权力关系和欲望。
翻看观影历史,惊奇的发现,十年前的六月份,我看了《去年在马里昂巴德》。
5 ) 关于《法兰西特派》杂志栏目标题的谎言
只能说韦斯安德森的天才是在我欣赏电影的天花板之上,巨大的信息量像洪水一般想我袭来,伴随着精心设计的画面、色彩、对白,这个将是一部两极分化很严重的片子,我内心对他也是爱恨分明,整部电影就是一部极其老练的艺术家的作品,却超出了观众娱乐性的体验。
我仰望着天才看完了这部电影,脖子有点疼…第一个故事“艺术与艺术家”专栏:一个贫穷的艺术家,因为正义的愤怒且不妥协被体制约束,而那个女警代表着规则,于是艺术家的艺术创造被约束在了这个女警代表着的规则的裸体上,其中有个片段很有意思,艺术家试图去修改女警(规则)的身体,于是艺术家的手被打开—他没有改变规则的资格,他只能在规则之内创作,当遇到创作瓶颈时,接受一次女警“规则”给予他的洗脑电击,之后关于他把内心挣扎的暴力美学完成在了束缚他的高墙之上,这样的作品,自然得到了利用和逃避规则的人赏识,他们坐着运送妓女和流氓的押送车,来到了监狱,那些人无比喜爱着这种无法冲破约束的暴力挣扎,这是一个阶层对另一个阶层戏谑般心灵的窥视,最后这个艺术家居然帮助那些罪恶的人摆脱了被规则压迫的愤怒人群的报复,于是获得了自由,这其实是一个超现实的政治话题,一个无奈的艺术家的自白,他思想被束缚的困窘,内心的挣扎,还有违心的妥协。
第二个故事政治\诗歌专栏:那位老处女记者就是那个戴头盔的女孩,画面黑白就是关于她面对年轻时爱人的想象,在想象中,她告诉年青的自己要改正的点点滴滴,最后当恋人死去,全世界只把男孩的肖像变成了抗争符号,只有这个当年的带着头盔固执的“女孩”保留着她的爱情;女孩年青的自己和现在的自己对话时,她们相互道歉,完成了一次自我的和解,但是男孩留给她的扉页留言,依然让她久久无法翻过去…这其实是个爱情故事第三个故事美食专栏:当年这个专栏作家身在异地,穷困潦倒,为了生存写一些迎合主流群体的语言文字。
作家作为有色人种,居然还写了反黑人主义的文章,于是在这个警匪故事里,主角依旧是白人,但他悄悄加入了一个他的影子,那个华裔厨师,那个迎合警察局各种要求的厨子,于是厨子用西方人惯性的思维的设定—那个毒盐制作的萝卜(其实是四川泡菜,但是美味在异乡认为是毒药),完成了警匪片中拯救人质的关键一步,这是有着一个巨大的讽刺意味的迎合,作者在自我审判着自己创作初心,他为了生存做了多少背叛自己的迎合,直到加入了那页扔进纸篓的故事核心,最后得到老板的认可。
这是一片关于人生的文章!
6 ) 2个观看角度+32部相关影片|《法兰西特派》超前测评|韦斯·安德森奥斯卡提名预定
(本文章可在我的B站和Youtube频道「小玄儿的深夜聊碟」观看视频版,欢迎点击)这个十月韦斯·安德森的影迷们,终于可以看到《法兰西特派》了。
今天跟大家聊聊一刷的观后感,以及大家看前需要了解的背景。
韦斯·安德森在电影节访谈里提到,这部《法兰西特派》的创作初衷,来自于他作为一个美国人,大部分时间都生活在法国。
于是他就有了一个想法,拍摄一个在外国生活的美国人的故事(as an American living abroad)。
基于《纽约客》这个杂志,让他想到可以做一个章节体的故事集合,这也是他最擅长的剧作方式。
蕾雅·赛杜也在采访里透露,她和韦斯·安德森都是法国新浪潮的影迷。
而这部《法兰西特派》更是献给法国电影的一封情书。
于是,我们就有了两个观看《法兰西特派》的角度1.韦斯·安德森对纽约客杂志和美国作家的致敬2.韦斯·安德森对法国导演和新浪潮电影的迷影情结整部影片还有赖于,剧组找到了这座位于法国西南部的小城 Angoulême。
韦斯·安德森说,这个城市有对的建筑,有趣的空间和独特的垂直堆叠。
他和艺术指导、美术设计一起,创造了这个电影里虚构的法国城市,并且邀请了城市里一半的人参与了电影的演出。
影片信息量之大,对白之多,很多观众看完都觉得,没有达到当年《布达佩斯大饭店》的观影高潮,究其原因主要来自三个方面:第一个是四个小故事之间是并列关系,不像布达佩斯大饭店的三层故事有明显的嵌套关系。
第二个是影片三个故事的叙述过程中,画面不断在黑白和彩色之间转换,第一次观看非常让人摸不着头脑。
第三个是影片的呈现形式,不断在旁白叙述和作者视角,定格动画,真人电影,以及二维动画中跳跃。
以上这些因素,导致我们第一次观看《法兰西特派》时眼花缭乱,完全跟不上节奏,只剩傻笑。
所以,这绝对是一部需要二刷的电影下面是我一刷后的个人解读角度仅供大家参考和讨论,为二刷做准备————————————————轻微剧透线————————————————让我们用不一样的方式打开这部《法兰西特派》观看角度1|以杂志为形式的观看体验与其说这部电影是章节体,不如说这部电影是杂志体。
这部影片的片头很短,定格动画展现杂志在印刷厂的流水线上印刷完成后,马上就进入了故事的旁白,介绍《法兰西特派》主编:Arthur Howitzer Jr. 的生平。
故事的主线从主编与编辑们的晨会开始,就进入了这本杂志的不同板块。
观众就像在翻看一本,刚从报刊亭买回家的最新期刊。
四个主要的板块由四位记者完成,关于城市、艺术、政治和美食。
影片致敬的《纽约客》杂志自创立以来,就遵循着高雅与幽默并存的基调。
在《法兰西特派》的电影中,每个杂志的板块故事里,也融入了不同风格的混搭。
超现实的在城市的过去与未来中穿梭抽象的艺术作品与艺术家的离奇人生美食大厨的毒药体验与绑架犯罪故事这四个板块的内容呈现形式完全不同,就像是你在看杂志里四个作者的文章,他们写作风格和报道方式也完全不同。
第一个故事是作者城中的骑行Vlog第二个故事是作者的TED演讲第三个故事是作者亲历现场的报道第四个故事是作者电视采访的回溯每当影片回到杂志社的现在进行时语境下,观众看到的画面会是彩色的。
每当影片进入杂志记者的讲述故事语境时,观众看到的画面会是黑白的。
就像是在阅读杂志页面上的黑白文字,当然杂志的每个板块也是有彩页的。
每到故事的精彩时刻,画面就会配合观众的想象,出现绚丽的彩色画面。
观看的体验就像我们自己在阅读杂志的时候,看到精彩桥段自己想象出来的颅内高潮。
最后一个故事中的二维动画部分,更像是纸质杂志里的漫画彩页,让读者有一种看到彩蛋的感觉。
梳理完杂志和故事的构成,我们来聊聊观看角度2|一封献给法国电影的情书电影的开篇就是对雅克·塔蒂的致敬,作为塔蒂的粉丝,我一秒高潮。
影片中大量的镜头横移,肆意打破影像空间的上下左右边界,让人想起戈达尔的电影《一切安好》。
最后一个犯罪故事的警察与绑匪枪战,让我想到希区柯克的《擒凶记》。
这看似好像和法国电影没有关系,但是想想法国导演们对希区柯克、比利·怀尔德,以及好莱坞经典电影的热爱,同时也影响了法国新浪潮导演们的创作。
如果你是法国电影的死忠粉,你绝对可以找到更多致敬和线索。
所以韦斯·安德森在这部影片的三层嵌套是翻看杂志的体验阅读美国作家书写的故事再通过法国电影的影像方式呈现出来韦斯·安德森将无人问津的杂志,作者扔到废纸篓的稿子捡了回来。
用当代观众喜闻乐见的日常Vlog、TED演讲、广播、小剧场、电视采访、动画片等等形式,将故事绘声绘色的重新展现在我们面前。
影片集合了韦斯·安德森之前动画片与真人电影的全部技巧。
让观众在定格动画,真人电影和二维动画的观看体验之间穿梭。
对称构图的画面、流畅的移动镜头,再加上一点点手持摄影,不断地提醒观众,这四个文字故事的影像载体,都是作者在场的讲述。
影片从《法兰西特派》的创始人Arthur Howitzer Jr.,作为美国《自由堪萨斯晚报》持有者的儿子,年轻时就去了法国,在那里创办了这本杂志开始。
影片结尾,随着主编的去世。
让观众阅读的这本杂志,成为了这份报纸增刊的最后一本。
影片通过对纸媒的缅怀,更是表达了主编对文字工作者们的溺爱。
主编的审稿串联了整部电影,他从不删减,只是任由这些出色的记者,随心所欲的写着自己的故事。
纵观小镇的兴衰史、艺术作品与艺术家、与名厨的一顿晚饭和意外。
每个故事看似符合板块的话题,但是报道内容,实则荒诞离奇。
其中一个记者甚至没有完成过任何报道。
《法兰西特派》中缅怀的是一个,文学和影像都充满创造力巅峰时代。
那就是1950-60年代法国新浪潮,卓越的文字工作者都拿起摄影机,成为了用影像讲故事的人。
片尾字幕最后也列出了所有致敬人物的名单,其中不乏美国作家:詹姆斯•鲍德温。
IndieWire更是列出了32部,影响了韦斯·安德森这部新片的电影“The Gold of Naples” (1954) Director: Vittorio De Sica“Boudu Saved from Drowning” (1932) Director: Jean Renoir“The Lower Depths” (1936) Director: Jean Renoir“They Made Me a Fugitive” (1947) Director: Alberto Cavalcanti“City Streets” (1931) Director: Rouben Mamoulian“Shoot the Piano Player” (1960) Director: François Truffaut“White Nights” (1957) Director: Luchino Visconti“Life Dances On” (1937) Director: Julien Duvivier“David Golder” (1931) Director: Julien Duvivier“Touchez Pas au Grisbi” (1954) Director: Jacques Becker“La Chinoise” (1967) Director: Jean-Luc Godard“Quai des Orfèvres” (1947) Director: Henri-Georges Clouzot“The Man Who Knew Too Much” (1956) Director: Alfred Hitchcock“The Hole” (196) Director: Jacques Becker“Masculin Féminin” (1966) Director: Jean-Luc Godard“Mon Oncle” (1958) Director: Jacques Tati“Playtime” (1967) Director: Jacques Tati“Sweet Smell of Success” (1957) Director: Alexander Mackendrick“Casque d’Or” (1952) Director: Jacques Becker“His Girl Friday” (1940) Director: Howard Hawks“The Murderer Lives at Number 21” (1942) Director: Henri-Georges Clouzot“La Vérité” (1960) Director: Henri-Georges Clouzot“The Fire Within” (1963) Director: Louis Malle“Love Me Tonight” (1932) Director: Rouben Mamoulian“Painters Painting: The New York Art Scene 1940-1970” (1972) Director: Emile de Antonio“The Rules of the Game” (1939) Director: Jean Renoir“The 400 Blows” (1959) Director: François Truffaut“The Tenant” (1976) Director: Roman Polanski“My Life to Live” (1962) Director: Jean-Luc Godard“Irma La Douce” (1963) Director: Billy Wilder“One From the Heart” (1982) Director: Francis Ford Coppola“The Red Balloon” (1956) Director: Albert Lamorisse而观众们在影片结束后,更是不自觉地陷入影片的最后一幕。
那就是观看之后的无尽讨论,如果你也是想跟人讨论这部影片,留言说出自己的观点和看法,再聊聊法国新浪潮与喜欢的美国作家,那导演的目的就达到了!
最后提示一下《法兰西特派》里致敬的雅克·塔蒂、希区柯克和大卫·林奇。
我的B站频道里都有单独的电影收碟节目,喜欢的同学不要错过!
感谢你看到这里,好电影和书一样值得被反复观看。
我们下期再见2021年10月29日小玄儿记如果你喜欢我的文章,欢迎在 B 站或 Youtube 关注「小玄儿的深夜聊碟」每周分享新片测评与CC电影蓝光套装严肃影评|《驾驶我的车》看过这部电影后,你会有一点点不一样。
蓝光碟收藏|雅克·塔蒂 TATI|景观社会里的小人物|视听的愉悦与观看的自由蓝光碟收藏|双峰剧集+电影套装|大卫·林奇的影像世界蓝光碟收藏|希区柯克15部电影|终极版蓝光套装你的关注和评论,就是对我最大的支持!
7 ) 《法兰西特派》片尾的杂志封面
“All grand beauties, withhold their deepest secrets.”
——————————————————————————————————————————— newyorker风格的插画封面,但因为是虚构,可以天马行空地插入更多不合适的主题,wes真的是用心了。
8 ) 安德森三角形的一次失败的作品
安德森的电影在剪辑方面是我最欣赏的,从来不拖泥带水、语言画面和故事天衣无缝的契合、感觉没有一分钟的浪费。
不过安德森在导演了犬之岛、尝试了动画片的风格之后就有些走火入魔了,电影的画面越发向虚拟化和布景化发展,一味的强调视觉效果。
他果然在这部片子里展现出不一般的效果,特别是黑白彩色之间的切换、还有把城市风光用背景板来制作,很多场景有那么一种舞台剧的感觉,在一个虚构的狭小时空里、反而给了演员充分的发挥空间,我感觉几位老戏骨飙戏的异常开心。
也不是说这部影片的故事讲的不好,起码第一个小故事就很精彩、在我看来安德森仅仅拍了三分之一的好片。
语言本来是安德森的强项,如同滨口龙介的影片特色就是看似啰嗦其实很值得玩味的台词,毕竟滨口导演是东大文学系毕业的。
安德森在早期的几部片子里的台词都有非常工整精致和诙谐的,法兰西特派里完全丢失语言表达上的美感,甚至影响了观众对影片的理解。
从整体上讲,安德森的艺术特色是语言、剪辑和构图上的对称统一,如果其中某一个元素不到位、会影响整部影片的观感。
法兰西特派里的剪辑依旧凌厉,构图上更不用说、简洁和高对比度在视觉上给人以极度的舒适感,唯一的遗憾是对话的苍白无力。
即使如此我还是佩服导演的调度能力,这么复杂的故事线和时空跳转的急转身,安德森统统放进去了。
我期待安德森三角形的下一次成功。
P.S. 蕾雅·赛杜最近红的不成样子啊,我心目中的女邦德在片中大胆出演,果然美的一塌糊涂,我觉得第一个小故事完全可以让她和边境杀手的那个男主演丰富成一部大片,可惜了。
9 ) 论如何优雅漂亮又让人极度舒适地不好好讲话。
明明可以用纸巾和火柴画一幅惟妙惟肖的麻雀,但却偏要用胡乱的涂抹来展示最爱的女人;明明是肤浅、躁动着的荷尔蒙的欲望,但却偏要拉上一座城和政治哲学思想来倾覆与对抗;明明最想说的是对于每个“他者”孤独灵魂的慰藉,但却偏要把篇幅都留给惊险的警匪大战;明明是电影,但却偏要像本杂志。
明明随性潇洒,但却偏要井然有序。
明明有深沉地爱,但却偏要漫不经心。
而最重要地是,要看起来,像是故意要这么做的。
10 ) 恋物癖韦斯·安德森的玩具盒子
韦斯·安德森的电影,是玩具屋?
是拼贴画?
是故事绘本?
是微观模型世界?
还是玻璃瓶里的船?
这一系列标签,似乎都可以导向完全相反的两极。
你可以认为,这些标签意味着一种幼稚、做作、刻意、匠气的风格,也可以认为,它们意味着一种可爱、天真、繁复、精巧的美学。
看完韦斯·安德森的新作《法兰西特派》,我有一种感觉,安德森已经把这两种完全相反的评价合二为一,让两者矛盾但又不失和谐地并置在一起。
一方面,当一帧接一帧精美如明信片般的画面目不暇接地不断涌现继而消失之际,当一个个耀眼的明星在银幕上一闪而过甚至来不及说出几句完整台词之时,那种过量的美感、让人不由得慌张起来:这未免太过铺张、太过奢侈了吧!
这样不知节制地过度堆砌,让人来不及细看、捕捉、记忆,也因此对这种浪费——对美、对风格的浪费——有点生气。
另一方面,《法兰西特派》又创造出一个小小的宇宙,如万花筒般闪闪发光、色彩绚烂、变化莫测,镜头每切换一次,就如同转动了一下万花筒,让人产生一种美好的眩晕感。
献给纸媒的一封情书?
一曲挽歌?
《法兰西特派》以韦斯·安德森痴迷的《纽约客》杂志为灵感,采用章节式结构,呈现杂志不同版块的故事,由“讣告、旅行指南和三篇专题文章”组成。
三篇专题文章来自艺术/艺术家、政治/诗歌、美食这三个专栏,通过三种叙事风格讲述了三个传奇、幽默的小故事。
杂志的开头是一则讣告——《法兰西特派》杂志创刊人兼主编小阿瑟·霍维策的讣告。
但这则讣告却没有阴郁灰暗的调子,而是采用轻快调侃的笔调所做的一则人物速写,讲述主编的传奇人生与性格。
他是一个热爱法国文化的美国人,一个宠爱纵容作者的主编,他的格言包含一种冷幽默,比如“尽量让它听起来像是你故意那样写的”(just try to make it sound like you wrote it that way on purpose)、“no crying”(不要哭)。
这两句格言,不也是韦斯·安德森自己的创作目标?
一种精心设计、风格可见的轻喜剧。
接下来的“旅行指南”是一则轻松愉悦的城市素描,通过流动影像呈现出法国小镇的迷人空间,通过定格镜头的并置表现出小镇历史与当下的变迁。
三个故事都充满了混乱、暴力、忧伤、诗意、美,是韦斯·安德森对于法国的浪漫想象与传奇怀旧。
第一个故事《混凝土杰作》是对现代艺术作品的诞生/经典化过程的一次温和嘲讽。
一位因杀人罪被判终身监禁的疯子天才艺术家,在向他的缪斯女神、狱警西蒙娜求爱被拒绝后获得灵感,再次拿起画笔。
一位狡猾、贪婪但有些独特艺术眼光的画商,通过在艺术界各种玄妙的运作,将艺术家捧上了现代艺术的神坛。
第二个故事《宣言的修改》是对1968年巴黎“五月风暴”的一次浪漫怀旧。
中年单身的美国女作家为了一次时政报道,卷入了一个年轻英俊的学生(甜茶)的政治/感情生活,故事中有一个酷似戈达尔《中国姑娘》中维亚泽姆斯基的年轻巴黎女孩。
安德森借孤独的女作家之口,说出了《纽约客》一位著名作者对巴黎学生的一句颇有意味的评价:“年轻人感人的自恋”(the touching narcissism of the young)。
第三个故事《警察局长的私人餐厅》是对巴黎美食传奇的一次异想天开的想象。
传奇关于一位天才厨师,但整个故事却是一部黑色电影,充满暴力、阴谋、绑架、毒杀,包括一个黑帮会计师、一个绑架者、一个卖艺女郎、一个警察局长和他冷静、成熟的儿子。
故事作者(以美国著名作家詹姆斯·鲍德温为原型)出于一种含蓄的美学考量,删掉了故事中最关键的一个情节:用有毒的萝卜杀死了犯罪团伙但自己也险些中毒身亡的传奇厨师,念念不忘的是一种他从来没有尝过的味道——毒萝卜之味。
这些故事充满了密集对话、独白、旁白,每个故事都以不同的美学风格被讲述。
安德森似乎想要穷尽所有视觉风格——黑白/彩色、宽屏/窄屏、静照/动画、定格/升格、对称构图/上帝之眼,他不知疲倦地在这些无限选项之间不断切换。
我们看得头晕目眩,他却似乎始终亢奋。
最终,他将自己迷恋的巴黎,那个亨利-乔治·克鲁佐、雅克·塔蒂,戈达尔电影中的巴黎,那个《纽约客》杂志中的巴黎,一个充满梦想、艺术与美的城市,变成了若干璀璨、耀眼、易碎的玻璃球,小心翼翼地珍藏起来。
玩具盒子,而非现实渐近线《法兰西特派》中,韦斯·安德森的恋物癖、收集狂、细节控、强迫症,到了一种近乎狂热的程度,超过他之前的所有作品。
如果说早期的安德森,依然对人类充满混乱的内在情感世界感兴趣(《青春年少》《天才一族》),那么,在晚近几部作品中,他更加清晰地确定了自己的兴趣——搭建一个包罗万象的微观世界。
短篇故事集的多样性、松散性、丰富性,也确实更适合展示他的美学风格。
所以,那些对于他的评价——玩具屋、拼贴画、故事绘本、微观模型世界,虽然或多或少带有评论者的一丝轻慢(也许并非恶意或批评),但这些也许正是安德森所不懈追求的目标——把一切他所迷恋的美好事物,统统放进自己的微观世界。
无论是具有实体的物品、空间(场景)、人(电影明星),还是抽象的视觉风格、叙事方式,或者他一直喜欢的电影、杂志、小说。
一切都变成了他的收藏品。
于是,也就很容易理解对于韦斯·安德森的各种批评,这些批评基于一种传统的现实主义美学观。
对于大部分当代艺术电影而言,一个更被推崇的创作准则是,电影是现实的渐近线。
虽然有卢米埃尔(现实主义)和梅里爱(幻想)这两条脉络,但当代艺术电影早就远离了“梅里爱—表现主义”这一脉络,而更倾向对现实进行模仿复现。
韦斯·安德森早早放弃了现实的渐近线这一准则,他以孩童一般的天真想象、强迫症一般的一丝不苟、造物一般的野心与精力,去追逐另一种艺术理念——凭空创作一个属于他的玩具屋,使其成为对于世界的一种精美、微缩的复制品。
但他的原则不是现实主义,他的原则是美。
韦斯·安德森的美学更接近美国伟大的现代主义艺术家约瑟夫·康奈尔。
康奈尔的作品通常是一个正面是玻璃的盒子,里面装着他拾得的物品,如软木球、照片、地图等等,这些他从廉价货摊、纪念品商店、图书馆、电影院、画廊收集的小玩意儿。
他在盒子这一几何格式中细心组合和编排他的物品,在盒子中创造出了个人的世界。
韦斯·安德森的几何格式就是镜头边框,他在这个严谨、稳定的框架中,以无比的精准来规划一切。
他的电影如同一个精密的钟表,是一种精巧的电影装置,似乎包含着一百万个微小的部分在同时运作。
他包罗万象的玩具盒子中,装入了无数现实的美丽碎片,这些碎片所拼凑起来的现实拼图板,不是完整、逼真、写实的,而是怀旧、幻想、浪漫的。
所以,一个现实主义者,也许很难接受韦斯·安德森精致、美丽、感伤的玻璃盒子,于是会对他的风格手法产生质疑,觉得他的致敬是轻浮的、他的思考是肤浅的、他的创作是逃避现实的。
《法兰西特派》中,安德森用一种狂热的激情,致敬模仿各种经典电影、动画片、艺术品、社会运动、《纽约客》杂志等。
但这些致敬与模仿,似乎徒有其美丽的外表、却失去了原作的精髓。
对塔蒂的致敬,有塔蒂散点透视的复杂精巧,却没有塔蒂对于现代性空间的敏锐捕捉。
对亨利-乔治·克鲁佐的致敬,有克鲁佐的黑色光影,却与克鲁佐作品阴冷绝望的内核背道而驰。
对《纽约客》杂志的致敬,有《纽约客》的机智、幽默、时髦,却没有《纽约客》犀利、严肃、深刻。
但是,喜欢这种精美微缩艺术品的观众,就能原谅安德森的所有缺陷。
也更加能够感受安德森的优美,一种来自于实在感、秩序感、稳定感、繁复感的优美。
他精准掌控镜头中的一切,物体的颜色、纹理、形状、位置,人物的发型、服饰、妆容、姿态,甚至是说话的语气。
他对于视觉的一切偏执坚持——精心的构图、对称的画面、严格处于正中间位置的摄影机、一再重复的俯视镜头(上帝之眼),也就变得很容易理解了。
康奈尔的“盒子系列”诞生于二战前后,在那个充满不确定性的时代,这一带有怀旧情绪的、收藏癖般的创作方式,提供的是一种情感上的避难所。
在当下这一高速发展的数字技术时代,在这个一切虚拟现实都被体验为真实的赛博格时代,韦斯·安德森用物,对抗即将吞噬一切的虚拟世界。
他以一种固执、怀旧、浪漫的恋物癖,不厌其烦地用他的收藏品——坚实、稳固、确定的物——建构出了一个实在的微观世界。
( 原载公众号“虹膜,12月18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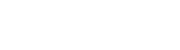




















































































看不下去,这种爆炸式的文本信息填充和场景搭造我不认为是好电影的样子
目前比较需要这样精致过度的作品让我拥有短暂的自我沉溺//韦斯安德森不断在强化自己的风格 新片总是更加的“集大成” 一部成片就是一座韦斯安德森主题公园//熟脸躲到要数星星 有点怀念大家初相识的时候(不是//他在文字和影像间找到的平衡大概就是这样 一些电影史的巧妙化用 还是法国人的电影有意思//彩色的部分还是糖果感十足 而黑白部分似乎是试图让人严肃起来//和1的远程观影
总感觉对于wa的评价一不小心就会陷入犬儒:一种风格,无关对错。越来越感觉走向了罗伊安德森的一体两面。罗伊安德森在静滞中寻找资本的本质,一种极简的向量式的顺滑运动剥开了一次荒谬完成背后的恐怖力量。而wa更偏爱用机械性的运动生硬地衔接起顺滑的影像段落,在这种矛盾中营造出一种虚假的繁华,法兰西特派就是集大成者,戏里戏外都是如此,形式的杂糅真正呈现了资本僵死前的绚丽表象。
睡着了…
看了二十分钟,回来看豆瓣评论,发现电影和评论都看不懂,好吧,我太肤浅了,只能看到画面的色彩,看不到影片的实质,看到了豆瓣长评短评的每一个字,却几乎看不懂每一段话。如果拍的东西,写的内容,普通大众无法接受,也只能是这些人的自嗨罢了。。。
电影本身不至于一星,但我期待了不知道多久,考完试立马来看,结果看到这么个玩意儿,啊!
画家会记得涂了松节油胴体的样子,学生会记得吻了千遍嘴唇的气味,男孩会记得绑匪唱摇篮曲的声音,厨师会记得萝卜里毒盐的味道。商人可以用运输机将混凝土壁画运到美术馆,却无法让他们相爱。彗星可以沿着轨道飞向宇宙外延,却不能阻止少年死亡。警察可以从劫犯手里解救人质,却无法治愈异乡人的乡愁。
快收场的21年,终于有部还算能看的了,真·“永安镇”故事集。
形式和内容难得高度结合了
每个人物都如同乐高小人一样被插在原地然后精准走位,无休止地掉书袋讲一些无聊的自以为有内涵的故事,毫无情感和联结,观众面对本作就如同那些所谓的收藏家面对监狱艺术家那一幅幅不知所云的画一样,结尾终于把本片变成了绘本,那一刻我认为导演终于找到了最适合他的表现形式。所以蕾老师高难度艺术体操式的几个果体动作究竟有什么意义?
“now he looks like a corpse” 尽量让观众看出是故意这么书写——一句油滑的托辞,然后大可轻浮地用精致(但实则臃肿的)糖衣裹上这个时代已经不需要的一种浅俗的怀旧。#GoldenSceneCinema
很喜欢。看过最好的短片集之一。既然安德森言明了这是对【杂志】的银幕戏仿,那对这部电影抱有【小说】式观影期待的观众,是不是应反思自己搞错了文体?何况,它除了是副刊“法兰西特派”,更是安德森美学的最佳说明书:鲜丽明快的马卡龙配色;冷幽默、神经质、抑扬调的对白;强迫症式的对称(而几乎所有对称构图里又都包含一点精心设计的打破对称的元素);从台词到媒介手段的穷举法,当然还有安德森传统的悦目圆润字体。在三大电影节那堆丧逼片里,它是有趣、舒服、欢快的一股清流(除了台词有点密集,对大银幕不友好,但流媒体看可以暂停啊)。你们干嘛不爱它啦。
两星半。《纽约客》评出的年度最佳电影果然名不虚传。韦斯·安德森生涯倒数。
细究韦斯安德森的美学系统并非全然独创,多少都存在雅克塔蒂的影响,而后者面对自己创设的美学景观始终保留着独立的意识和探秘的观看眼光,一种失控的轨迹随机地弹射出去并从局部去拆解那些装置,装置结构的破坏内涵的象征性生成幽默感,而非像韦斯这般沉溺其中,因此他后期的几部电影虽然不算工业意义上的商业产物,却是美学意义上的工艺商品。
雨夜,一边小酌,一边看这样的片子,才叫欢心。跟随专栏作者的视角,用影像来诠释一本杂志,这是属于韦斯安德森的文学电影了。前两个故事非常好玩,最后美食那个稍显乏味,看来还是艺术和政治更吸引我。最后嘴一下,年轻人还是要多做爱。因为只有做爱多的人老了才有资格后悔,做爱少的人老了以后连回忆的素材都没有岂不是很可悲。
画面音乐堪称一绝,每一帧都能做成海报,很多地方配乐节拍都和画面动作同步。喜迎新春的好节目,可惜这么多一流演员的表演已成定势,剧情过于简单,并不精彩巧妙,形式太大于内容。。。
我理解这片子想要表现从异国视角看世界带来的奇趣/新生感,同时精心安排覆盖了法国的种种美德。但是看起来真的太累了,眼耳并用才跟上巨量的旁白,文字还特别扭捏,看得我心慌气短。简单来说就是看幼儿园汇报演出的那种“孩子的世界很美好很动人,但是我老了”的感觉。
这世界缺少这个,无聊无用且美的诗意。
相对于一部电影来讲在美术上画的功夫太多了,如果有简洁的故事就能成功,这部明显是失败的叙事
UGC Danton 时不时蹦出的奇思妙想还是会让人忍俊不禁,喜欢女郎的蓝色眼睛和清唱的A la claire fontaine。但全片就像个做工精巧、价值不菲的积木玩具,虽然高级但我只会简单地摆弄,不一会儿就玩腻了。